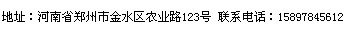无意间撞破父母现场直播,该怎么面对父母
我发现肌肉男大部分欲望都很多,比如说我继父,经常没事就把我妈妈往卧室里拉。
昨天我回家的早,去阳台上晾衣服,路过他们卧室。结果衣服还没晾好,他们就进来了,还特别的急不可待。
我不好意思出声,就在阳台上看了整场现场直播……
现在,我已经无法直视他们了,我该怎么办?
我叫苏扇,出生在沿海F省的一个小渔村里。
出生之后,我的大部分记忆都是在船上,我姆妈就是船上的一只“羊”。
村里的男人一出海就是几个月,很少能够靠得了岸。一群身强力壮的男人围在一块,憋上这么久,总会闹出点事情。于是早年间,聪明的向导就在出海前买几只小羊,火泄了,船也满载而归了。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羊就变成了真正的少女,有些家里生的女孩多,就会主动把女孩送过来,换上点花销。
我姆妈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她就上船当了羊。
十八岁的时候,姆妈在船仓里生下了我。连她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有的,更别说是谁的种了。
姆妈姓苏,没有名字,大家就喊她苏么。
满月之后,我也没有名字,她不识字,看见我手里抓着把蒲扇,就叫了我扇子。
有了我之后,姆妈的跑船生活依然没有改变,白天做个厨娘,晚上也继续用身体工作。
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也能朦朦胧胧感受到,夜晚是那么的漫长,和恐怖。
底板下面狭小的货仓,连续不断的男人的脚步,低低的喘息,摇晃碎了一汪水中的墨蓝倒影……
姆妈让我剃光了头发,打扮得像个男孩子,专门守在锅灶旁给她生火。长到十岁了,我还是又干又瘪,成天脏兮兮地像个泥猴。
有一天,是个暴雨夜,船是不能前行的,抛锚停在了一处浅滩。
船舱里到处都是湿哒哒的,可是不能阻拦男人们下来货仓的脚步。
一个连着一个,不断地来。
几个男人出了火,还不肯走,使唤我给他们烧壶热水冲茶吃。
我小心地绕过虚软的姆妈,捧着茶壶走过去,却不小心绊倒,将热水泼了一地。
匆忙擦地的时候,有个男人突然说,苏么的女娃长大了。
跑完了这一趟,姆妈就下了岸,带着我去了小县城里。
我问她,为什么不上船了。
她看着我,说不能再让你也当羊。
那时候我有点明白,又有点不明白。现在想来,羊的女儿,哪里逃得脱这样的命。
离开那条船,还会去一艘更大的船上,任人宰割。
小县城里谁也不认识我们母女俩,它只认钱。姆妈的钱花得很快,还需要一直给家里的三个舅舅寄钱,所以日子过得很辛苦。
半年之后,姆妈结婚了,嫁了个四十出头的鳏夫。
男人叫章建松,个头不高,却很壮实,在县城里当个消防员。
其实我记得他,他常常会来出租屋里找姆妈。但我很害怕这个一身黝黑肌肉的男人,每次他一来,总会折腾得姆妈病好几天。
结婚之后,我和姆妈搬到了章建松的房子里。他家住在一片低矮的平房里,两条小巷住了二三十户人家。油腻腻的大门一关,里面的住客从黑黢黢的窗户缝里往外看人,眼睛里不知道在打量些什么。
章建松上班很忙,还喜欢喝酒,每晚回来都是醉醺醺的。一进家门,不管姆妈在干什么,抓住她的脖子就往房里拖。
常常到了半夜,我还一直能听到姆妈像猫一样细弱的叫声,心里像吃了路边野生的青杏一样,酸得发苦。
姆妈是夏天时候进门的,到了第二年夏天的时候,就生下了一只烫光了毛的小猫仔。
姆妈告诉我,这是我弟弟。
我看了眼那团肉红色的东西,只觉得好丑,可姆妈却开心坏了。
姆妈怀孕的时候,章建松都没有放过她。但是进了月子,姆妈没办法继续伺候,家里就时不时传来打骂声。
“不给碰老子娶你干什么,要不是老子,你还在外面站街呢!……哭哭哭,一屋子的丧门星!”
躲在房间里,我听着大门哐当一下甩上,心里一颤。
我不知道,这一巨响,彻底终结了我无知的童年。那之后,我面临的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无边黑暗的泥沼世界。
那一天,我还记得,是个阴天。
弟弟阿伟从夜里就开始发烧,哭了一夜了,姆妈带着他去了诊所挂水。我留在家里,给继父温饭。
不一会儿,章建松回来了,听说姆妈走了,暴晒一天的黑红脸庞上满是怒气,“这臭婊子,就知道花老子的钱!”
用嘴咬开啤酒盖,发出蹦一声响,他仰头咕咚咕咚地喝起来。我哆嗦地站在一旁,竭力贴紧墙根,想让自己存在感再弱一些。
几瓶酒喝下肚,章建松显得有些醉了,他突然朝我招招手,“你,叫什么?”
我怯生生地说,“扇子。”
“你过来。”
我不敢去。
他瞪眼,“老子是你爹,还能吃了你吗!”
站在他身边,闻着他身上的汗味儿和酒味儿,我两条细瘦的腿肚子都在打转,整个人抖个不停。
他先是用玩味的眼神上下打量了好几圈,一边看一边笑,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紧接着,两只蒲扇般的大手摸了上来,开始在我身上游移,尽往衣服的缝隙里钻。它们像条毒蛇一样,越滑越深,舔着我的皮肤。
章建松笑眯眯的,露出一口黑黄牙齿,“小扇子也长大了,学会伺候人了吗?”
这是我第二次听到长大这个词,也让我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这个词背后的危险。
我扭着身体,微弱地抗拒着他的抚摸,让他不要弄我。
可是他的力气太大了,一把将我搂进了怀里,更加放肆。
他两只胳膊,一身腱子肉,铸成了一个钢铁牢笼,我根本无法挣脱。
破旧的睡裙早就成了布条,章建松贪婪地逡巡着我瘦小的身体。我虽然不懂,却还是有羞耻心的,伸手挡住。
“章叔叔,放开我--”
他一直挂着笑,手揉得我生疼,“喊爸爸,知道吗?你可比你妈干净多了,正好,这段时间好好陪陪我!”
听到姆妈的名字,我这个溺水的人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开始不停地哭喊着“姆妈”。
“来,让爸爸看看,这儿长得怎么样了。”说着,就开始掰我的手腕。
就在这时候,大门打开,姆妈抱着阿伟回来了。
她看着这场景,一下子僵在原地,缺少血色的嘴唇不停发抖,“建松,你、你--”
我只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眼泪刷地就掉了出来,扑向门口的动作被章建松一把按住。
他不但没有惊慌,反而更加恶狠狠地在我腰上掐了一把,“怎么了,你们都是老子养的,摸还不能摸?”
几秒钟之后,姆妈做出了一个让我没有想到的举动。
她缓缓关上门,然后抱着弟弟回了房间,就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
我痴痴地看着她,“姆妈……”
她却没有看我一眼。
最后,章建松将奄奄一息的我扔在地上,踉跄着回了屋。他说我还小,以后有的是机会。
躺在地上,我浑身都火辣辣的疼,心里更是难受。
他说的没错,从那之后,这个家就变成了魔窟。
每次回家,他都会故意来堵我,阳台上,厕所里,甚至到后来就直接在客厅里动手。
他乐于揉弄我,看我挣扎,不停地给我带来疼痛。
我每天都像一只瑟瑟发抖的麻雀,东躲西藏,心惊胆战,却还是躲不过偷猎者铺天盖地的罗网。
有一次,他甚至将我扒光了,按在卧室的床上。而旁边,就是姆妈和喝奶的弟弟。
章建松将我压到姆妈的胸前,逼我和弟弟一起吃奶,然后自己压到了姆妈身上。
从始至终,我的姆妈都没有反抗过一句。
心满意足地拉上拉链,章建松将粘稠的东西抹在我的脸上,他居然还在笑,扬着眉,好像个上帝一样。
不停地擦着脸,脸上都被我擦破了皮,我带着哭音,第一次质问姆妈,“为什么?”
她双目无神地躺在床上,弟弟还闭着眼睛吸着奶水。
“扇子,你听话,不要让姆妈难做。”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章建松的行为叫做猥亵。不过在我还懵懂的十二岁,已经提前感受到了绝望的滋味儿。
抓起地上揉成布条的睡裙,我光着脚跑了出去。
跑到了一片荒滩,缩在杂草里,我把头埋在胳膊里,不停地哭。
外面的世界早不是小小的一条渔船,我也无法在恐惧的时候缩进碗柜中保护自己,我甚至连保护两个字都不会写。
这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的天是黑的。
也是在这一天,我遇到了第一个改变我一生的男人。
我哭了一会儿,还是不想回家,就痴痴地看着眼前的浅滩。
这里原本是一弯湖泊,这些年不断有人往里面扔垃圾,渐渐地断流,就剩下了一片浅水滩。大人们很少来这里,孩子们也不喜欢杂草里咬人的飞虫,所以我把这儿当成秘密基地。
夜晚天空很黑,星星也很亮,倒映在水面上,让我想起了从前出海的日子。
正在我发呆的时候,浅滩里猛地冒出一个黑色的脑袋,打碎了这片星光。
我吓了一跳,一屁股跌坐到身后。
黑色脑袋慢慢升高,变成了一个年轻的男孩。他浑身只穿着一条短裤,像一条游鱼,浑身都湿漉漉的。
他走到我面前,我仰头看他。他很高,比章建松还高半个头。眼睛是一双三角眼,鼻梁挺直,嘴巴红红的。
他给了我一脚,“起来!”
这一脚踹到了我的肚子,我一疼,万般委屈又钻了出来。为什么所有人都欺负我,难道我就这么招人厌吗?越想越伤心,眼泪成串地往下掉起来。
男孩不理我,就和抓小鸡一样给我甩到一边,捡起了被我压住的衣服。
穿好衣服,他走到我面前,三角眼里满是凶悍,“这是我的地盘,以后再看你过来,我就打断你的腿!”
抽噎着揉着脸,我呆呆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直到那个小黑点完全融入夜色,还是不肯挪开视线。
那时候,我心底涌出了一股艳羡到极点的情绪。
这个男孩,他是那么自由张狂,无所畏惧。他看起来那么蓬勃有力,浑身散发着勇敢的气息。
我对于他的追逐,始于崇拜,也终于崇拜。
之后一段时间,章建松变得忙碌了一些,加上姆妈出了月子,他折腾我的次数少了很多。但我还是不敢出现在他面前,他盯着我的时候,像要剥皮抽筋,总让我发抖。
而那之后,我开始常常见到那个男孩,也知道了他的名字,叫嘉仇。
嘉仇没有父母,跟着外婆一起生活,比我大3岁。他的外婆已经七十多岁了,驼背得很厉害,整个人缩成了煮熟的龙虾,大家都喊她驼阿婆。
用现在的话来说,嘉仇对年仅12岁的我来说,就是心里的男神了。我开始时时刻刻地北京那家医院治疗白癜风呢北京治疗白癜风比较好专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