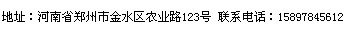lt特朗普如当总统有人直播吃翔,有人
坚持健走10公里第24天打卡报到,大选比较热闹,有人说如果特朗普当上总统,愿意直播吃土、直播吃翔,太重口了,吃瓜群众不嫌事大,坐求直播地址...
今日推荐《五月》上,作者:田中禾,河南南阳人,作家。
走进村,正是半后晌。乍看.村路那样窄,坑坑洼洼,全不像原来的样子。小时候她们在月亮地里玩,觉得这路是很宽的,很平坦。树把路遮严了,树荫很浓。路面上,雨水冲出浅浅的沟壕,长满狗尾草。车辙里散落着闪闪发亮的麦秸,谁家已经开镰割麦了。这是一天最安静的时候,没有人声、犬吠,老母鸡叫蛋也像离得很远.隐隐约约。她走近自己的家。板打院墙经几番风雨,颓堕成一溜黄土堆。受了她的脚步惊吓,一群麻雀从院里飞起来。墙根的阴凉里,满头白发的奶奶坐在断了拐肘的木椅里。“谁?谁啦?”奶奶朝大门口喊,用手搭起眼罩.吃力地望着。那大门,其实是两堆黄土留下的缺空,没有门楼,也没有门框门扇。香雨现在就站在那土墙的缺空里,两手在胸前垂着。抓着一个大提包,让提包蹭着膝盖。奶奶摸起身边的拐杖—一根劈口子的竹竿,身子做出挣扎起立的架势。“奶——”香雨喊出这么一声,眼眶有些湿润。奶奶愣了片刻,好像噎着了。她用拐棍使劲撑着,站起来,颤巍巍的,向前挪了几步:“是我的雨雨?”“奶——”香雨的声音又脆又颤,冲动的情绪在胸腔里升腾。“我的娃儿,你怎么这会儿回来了?”“嗳。”“不是说,你要上北京吗?”“不去了。”“乖娃儿,奶就不喜愿你去。奶八十四,春上害了几场病.怕见不着我雨雨。”“奶—”香雨拿白皙的手臂在脸上擦拭。她觉得一踏进家门,感情就变得这般脆弱,想扑进奶奶怀里哭一场。在奶奶眼里.雨雨是一条长长的淡灰色的影子,凭着黑黑的头发和白白的脸,长长的胳膊,才知道她在怎样站住。“瘦了。”奶奶用多皱的干巴的手捏着香雨的胳膊,用灰湿湿的脏袖子揩着干瘪的眼窝,伤心地嘟囔说:“娃儿是叫成堆成堆的书把你累坏了。”香雨终于流下了眼泪,一时哽咽,说不出话。她想对奶奶说.她考上了研究生,人家妒忌,不让去。可是,奶奶不懂这些,她无法向她说明白。从小,香雨就习惯奶奶的爱抚,它能把她心上的创伤抚平,抻展。可是这一次,她觉得谁也无法安慰她。香雨是个聪明沉稳的孩子。她好像从小就知道人活在世上不容易.需得拼了命去奋斗。在人们印象里,她总是细细的,瘦瘦的.默默地想着心事。无论得了人人赞扬还是受了训斥,总是一样地眨着深不可测的大眼,望着你。不笑,也不哭,不显高兴,也不显懊丧。从小学开始,她就是老师喜爱的学生。头几年,爹妈忙着家里无穷尽的杂事,并不在意孩子的学习。爹说,她被奶奶惯坏了.懒.笨,没有眼色,放了学,不知道帮家里干活,倒要妹妹去刷锅洗碗.喂鸡喂鹅,招呼弟弟。后来,有那么一天,香雨忽然对爹说.前村的民办教师春风考上大学了。“乡下人,考什么大学!”爹嚼着馍,蘸了辣椒,大口地吃,大声地吸溜嘴。“往后,乡下学生跟知青们一样,都能考学。分出来,一样干工作,吃国家粮。”“你那能耐行吗?想得恁美!”香雨没说话,奶奶却愤愤不平地嚷:“你就那样隔门缝看人!满庄子打听打听去,哪个不夸我雨雨行。年年都是……五好,是吧.雨雨?”雨雨没有做声,爹也没和奶奶抬杠,他照样嚼着馍。只是着意瞥了香雨一眼。从那以后,爹更多地使唤妹妹,不再吆喝香雨去干这干那。就在那一年,她被选拔进县中去读书,方圆三四个村,就选她一人。爹妈着实高兴了一场。虽然花那么多钱.把本来就穷的家挤得更干,可到底辛苦没有白受。如今香雨读完大学,分配到外省工作。是雨雨给他家争了脸,让弯腰驼背的爹,在人前高出几尺;使因为中风而手脚蜷缩的妈.成为全村最受称赞的贤德媳妇。雨雨,她是全村人的骄傲哩。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一个从小村里走出去的丫头,没有父为她经营,没有亲故可以倚恃,全靠自己去奋斗.那是如何的艰难。雨雨揿动轧水井的粗笨的手柄.轧出一盆清凉清凉的水。她觉得,这铁柄比以前更滞重,轧一盆水要喘几口气。她觉得自已烧锅技术不如以前.划了五根火柴才引着那些隔年的棉秆,使烟筒里冒出滚滚的黑烟。甚至她觉得奶奶那样用心用意为她藏着的腊菜也不如以前好吃。粗,嚼不烂,满嘴都是渣滓。从前的腊菜是酸溜溜的,很香,一边吃一边流涎水。太阳平西的时候,妈从地里回来。她第一眼看见她,觉得那佝偻的身材更显矮小.蓬乱的剪发更其污秽。一种凄怆的感情倏地涌上她的心头。“别,灰土狼烟的。”妈偏着身子,不让香雨去接她腋下挟着的一捆青草。香雨抢过去,一定要把它接过来。由于胳膊张得窄,刚刚到手.那草捆便骨碌地散开在当院里。“别.别.你不会。”妈一边挥手,一边蹲下去收揽。这时,她看见妹妹定定地立在大门口。肩上担着一担油菜秆,不出声地看着。“怎么?油菜打了?”她朝妹妹说,搓着手,不知该怎样帮她。妹妹不做声。她挤进大门,把担子撂下地,用手拨开妈妈,将地上的草揽好.用膝头压着,俯下身,双手使劲,勒紧草腰子,提起来,扔到院墙角去。“改娃子,你姐跟你说话呢!”妈拍着身上的土说。“听见了。”她说着,码好油菜秆,拿扫帚扫地。然后.拽一条毛巾.呼嗒呼嗒摇着铁柄轧水。“别理她.成天猫脸狗脸的。”奶奶用拐棍点着地,喃喃地对香雨说,“干一点子活,满院子盛不下她。有功!”“有功怎样?”小改突然大声说.“谁还能一天减我几顿嚷?没用的人,不兴多说,还不兴少说?!”她头上的两只蜻蜓辫子左右摆动,嘴里喷着白色口沫.声音激愤.一副凶悍的样子。奶奶毫不示弱地敲着拐棍:“恶!有本事!有能耐!说话都不让人说。我就说你有功,看你敢拿绳子勒死我!”“改娃,那么大丫头,不怕人家笑话。”妈继续拍打着身上的土,无可奈何地说。香雨从来就不会劝架.这会儿更有些不知所措,只是一声又一声地喊着:“妹!……奶!”好在改娃并没有继续争吵,气呼呼地拿毛巾在脸上擦了几下,哗地一声,把水泼得远远的.当当啷啷,把脸盆扔在院里,钻进西屋.呼通通关上门.再也不露面。“在场里,跟你爹抬杠了。”妈轻轻地叹息着。月亮升上树梢的时候,爹从场里回来。他说:“煮鸡蛋了吗?给雨吃。”便蹲在小凳上抽烟。开晚饭的时候.香雨想起弟弟:“爹,金成呢?”“进城了。”“进城干啥?”“谁知道他妈啦个×的,连高中都考不上,回来不干活。成天瞎窜!”晚饭摆上来。香雨敲着西屋门,叫了几遍,改娃说不饿,不想吃。爹一袋又一袋抽烟,抽了好长时间,啪啪地磕着烟锅说:“我们吃!,”接着,又愤愤地说,“种几棵菜,不够偷!大麦天,连个青菜都吃不上。”香雨看见爹的筷子总在碗里搅。她知道,改娃不吃饭.爹又气又心疼.吃不下。香雨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毕业一年了,没给家里寄过钱,爹总是说,如今日子好过,家里不要你的钱。你得攒几个,买表,买自行车,那是城里少不了的。她每天都在想着她的论文,从来没有想过家。直到这次回乡,她才给妹妹买了一套复习资料,一路上想了许多教训话,定要说服她,再复习一年,下些苦功……可是现在.她觉得这些话都可以免了。临睡时候.爹说:“南地的麦,我看行了。明儿早,就割吧。”大家都投做声。风轻轻掠过院子。嗒,一个杏子从老杏树上落下来。麦天,她喜欢听“吃杯茶”在黎明里叫。那鸟儿声音很嘹亮,上下翻飞,有时候翅膀就在你耳旁扇动,簌簌响。可是今天,她没能听到。她醒来时,一家人都下地了。猪在院里哼。厨房里有烧锅折柴的声响。窗户上一片金闪闪的阳光。脚头,奶奶早已起床。长时间不跟奶睡,不习惯,夜里睡得很不好。跳蚤在身下蹦跶,浑身痒痒。老鼠扑扑腾腾在身边打架,唧唧呻唤.听起来瘆人。一天一夜火车汽车的劳顿,后半夜困极了。等到沉沉睡去,天已经亮了。“奶——”在轧井旁漱洗着,她拿出从前惯用的口气嚷,“咋不叫我.让人家睡到这会儿?”奶奶的白发被灶门的火光映红。老人眯着眼,一脸皱褶高高隆起.专心专意烧锅。打从记事起,她习惯了奶奶做全家的饭。妈虽然蜷缩着手脚,却从未停息地里的活计。从前,生产队照顾她,派她拿竹竿坐在村边看鸡鸭。这几年,不再需要这样的活路,妈就像健康人一样下地种责任田。她看见奶奶站起来,双手抓着锅盖向上掀。吃力地掀了几次,才稍稍掀开一条缝。一股浓烟从灶口冲出来,差点熏着奶奶的脸。香雨跑过去,帮奶奶掀起锅盖。“如今不种桃黍,用木拍子,沉死了!”奶奶嘟噜说。锅里水沸腾着,箅上馏着白馍。这锅,跟他们学校教师伙房的锅差不多大小。以奶奶衰弱的身躯,她如何担得起这样重的担子,年复一年,趟过岁月的长河,如今八十四岁,还在照样干着。……在漫长的落着雪的冬日.奶奶拥着她.坐在被窝里。她哭,奶奶就从贴胸的衣袋里摸一疙瘩薯面窝头或是黄面饼子,在手里晃动:“甜甜,谁吃?”“我吃,雨雨吃。”“雨雨吃了亲谁?”“亲奶奶。”“雨雨长大养活谁?”“养活奶奶。”那般好吃的“甜甜”,总被奶奶的身子暖得温乎乎的。如今长大了.每月有五十三块工资,可她从未给奶奶扯过一尺布.买过一斤糖。昨天,她打开特意捎给奶奶的蛋糕,奶奶掉泪了。轻轻摸着圆圆的硬纸盒,不安地说:“要好多钱吧?你才干事……还有一桩大事没办。要仔细些。家里这二年顿顿有白馍,不要你惦记。出门在外,只管吃好.莫叫身子受亏。”当她为了那篇《中国农民的形成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伏案熬夜的时候,当她在学校领导的门前奔走,疲惫地为纠正一张不公正的鉴定表申诉的时候,强烈的欲念和恩怨充塞了全部的生活和思想,挤走了慈蔼的奶奶,挤走了所有过往生活的记忆。她把奶奶遗忘在九霄云外,甚至连做梦都不曾梦到过。她自责着,想要尽力帮助奶奶。和面、拌汤、调小葱、喂鸡、喂猪,把青草铺进兔笼,羊拴到村外。“唉,还是我的雨雨勤快,知道疼人。”奶奶坐进破椅,絮絮叨叨地说:“改娃子不成,乖孤得很,奶使不动。三天两头给家里怄气。西门外的大狗什么东西,她偏跟他好!”“什么,她和大狗吗?”香雨瞪大眼睛,不胜惊疑地问。“村里都闹得风风雨雨,你妈还舍不得吵她哩……”香雨不敢相信奶奶的话。奶奶自小就不喜欢改娃,她贪玩,不学习.考不上学,一家人瞧不起。可改娃才二十二岁.她小着呢。大狗都三十了,名声又不好。她会傻到那样?“奶,我下地送饭去。”奶奶想了想,脸上绽着笑:“担得动?”“担动的。”奶奶慢慢腾腾帮她把木桶洗刷干净,一头装汤.一头放馍,把一盆调小葱搁在馍上。“慢点。”奶奶扶着大门边的土墙望着。虽然她眼里只有一片灰蒙蒙的雾.但她却像能看见走远的孙女一样,凝神地立着。太阳在地平线上照耀,风荡过宽展展的原野。露水刚刚在草叶上闪耀,倏地,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金黄金黄的麦海被分割成破碎的方块。收割过的田里,麦个子一排排横躺着,人们在忙忙地蠕动。透过麦浪,可以看到攒动的人头或是弯弓似的身子。改娃直起身拧麦腰子,看见香雨趔趔趄趄担着挑子走来,就三步两步跨过去,把担子接过来,虽然她脸上仍然没有笑意,但香雨感到她此刻的情绪并不坏。金成也在地里干活。看见香雨,只是咧嘴笑。一年多没见.弟弟已经出脱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港衫,小喇叭裤,长头发。“吔,金成这一身,真够意思!”香雨笑着说。金成羞怯地看着姐,一时想不出话讲。“昨晚,啥时回来的?”“……总有十一二点吧?”小伙子垂了头,好像在地上寻镰刀。“十二点?”爹虎起脸凑过来,把鞋脱掉.垫在身子下坐着,“两点半!”“干啥么.那样忙?”香雨直勾勾地盯着弟弟。“嘻嘻,”金成又笑了.“电视投影《霍元甲》全集。最后一天。”“噢唷,我当你上夜大哩。”香雨讥讽地说。改娃正在擦汗,这时候嘎嘎地笑起来:“别看考不上高中.要是有个少林武术班,保险能考上。“金成涨红了脸,却没有认真生气。把嘴噘了噘:“也到集上买个圆镜镜,照照自个儿!还说人家!”“咋了?”改娃霎时板起脸.挑起眉毛,鼻子和嘴角都抽动着,声气十足地说,“十六七的小伙子,游手好闲,还不让说?别人不敢说,我偏说!十几亩地,往后,你得挑一半!谁该养活谁。”不等金成接腔,正在捆麦的妈从地中间走过来:“好了,好了!你姐把饭都送来了。吃!吃了干活。”金成把眉毛竖了几竖,瞥瞥改娃的神色,不知怎么的,不敢壮胆吵下去,把镰刀狠狠摔在地上.弯腰到桶里去盛饭。改娃迎着阳光站着。香雨发现她比过去更加成熟丰满。胳膊腿很粗实,肩头又宽又圆。尽管像每一个乡下女孩子一样贴身穿了小衣裳.胸脯箍得很紧,但那富于弹性的一对乳房仍十分显眼地高高隆起着。肥大的两胯把天蓝色涤纶裤子绷得紧绷绷的,好像裤缝随时都会坼绽。露水混着灰土,使她的裤腿和鞋子涂满黄色的泥浆。香雨觉得改娃已经成了一个棒劳力,再让她坐下来啃书本,是根本不可能了。“妹,吃。”她给妹妹捧一碗汤。“慌啥。”改娃并不接碗,自顾自地从从容容走到地头,撩起沟里的水洗脸。她探着身子,手在脸上噗噜噗噜抹,水珠迎着阳光,晶亮晶亮地从她手臂上滚下去。爹睃她一眼,粗声粗气地对香雨说:“你自己吃。”端了饭,低着头,咯噔咯噔,使劲嚼着小葱.好像在发泄自已的气恨。循着爹的目光,香雨看见,在改娃对面的沟坎上,大狗正站在那里朝这边张望。他家的麦子都撂倒了。一辆小四轮拖拉机在地中间停着,七八口人在装车,木杈挥舞,麦捆个个飞上车顶。一群劳力,粗手大脚地干活.粗腔大调地嚷叫.引得一地人眼巴巴地望。看见香雨望他,大狗趁势讪讪地踱过来:“大学生回来割麦么?老堆叔给你做什么好吃的?”香雨很客气地把碗伸着:“你先吃吧?”“你们吃,你们吃,我吃过了。”大狗对着香雨说话,眼睛不时地瞥着改娃。改娃板着脸,将湿手绢甩了甩,搭在乌黑的头发上,从大狗身旁擦过去,端起饭碗,转脸去吃。“老堆叔,这麦子不错哩。”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呼噜呼噜照样吃饭。大狗向前凄了凑,很神秘地压低声音说:“老堆叔,你可得赶紧些呀。……今年卖粮可难啦,得趁早……”爹仍然埋头吃饭,妈却沉不住气地凑过来问:“有啥消息吗?”改娃把饭碗敲了一下,大声说:“还用问他!我早说过了。你们不信。”大狗立刻接上话茬,郑重其事而又非常贴己地说:“西仓有三天就满了。东仓只收八万。今儿,明儿,敞开。后儿就凭条。再迟延.可卖不上了!”金成斜着眼说:“昨晚广播里还说要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呢.我不信打了粮食会卖不出去。”爹把饭碗撂在地下,闷声闷气地说:“就你话多!还不快吃了割!”尽管大狗听出这话是冲他来的,却仍然喋喋不休地说:“大叔。不敢迟疑呀。我家的麦,今儿就能打出来。吃过饭,叫小五把机器开过来.帮你割。晌午能上场,夜里一打,明个晒一天,后儿能卖。”“照你那么说.后儿不就凭条儿啦?我这脸面,哪儿去弄条儿?”“不碍的,我,我……给你想法嘛!”“算啦,还不起人情。”爹一边说,一边摸镰刀,弯腰去割麦。太阳升得很高了。尘土从爹的镰刀底下升腾起来,像一片飞舞的小虫。大狗尴尬地立着,慢慢摸出一支烟来抽。“三哥——开了!”远处.大狗的弟弟小五在喊叫。大狗嘿嘿地笑着:“婶子,啥时用车,说一声。”妈嘴里唔着。改娃站起来不谦不让地说:“别卖空头人情。要帮,下午过来。我们不白用,给钱!不帮,站远些。劳力弱也到不了让你们看笑话。”“好我的妹子哩,这说到哪儿去!”大狗慌忙地摇着头,说着,退走了。太阳一落.凉气就上来,一天的燥热慢慢消散了。月亮没有出.天黑乌乌的。风停了,树梢直直立着。田野里,有几只萤火虫悠悠地飞。远远近近,有些移动的光柱,那是拖拉机的车灯。电不来,麦场里静悄悄的。场边坐着一溜劳力,大家散散淡淡,蹲着、卧着。有人撑不住.跑到远处去抽烟。香雨侧身躺在麦捆上,嘴里嚼着一根光溜溜的麦莛儿。她旁边.是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石磙。累极了,好像全身关节都散了架,腰痛得折断了一样难支难熬,胳臂和脸面都在火辣辣发烧。“要蜕皮。”她想。在这种时候,她才懂得,默默躺着,不玩,不聊天,不看书,不想东西,是一种享受。她甚至盼望今晚电不要来。麦子是傍晚上场的。爹买了五盒烟央邻友帮忙,管了一顿像样的饭。如果电正常.两个钟头便可以收拾干净。这种50型脱粒机蛮好用,就是占人手,搬、解、喂、搓,要十几个劳力团团转。下午,爹差点和改娃吵架。刘家开了机器来,爹没有正眼看。小五呢,活活泼泼爱说爱笑的小伙了,那会儿也有些脸色灰暗。拖拉机跑了几个来回。改娃撵前撵后让烟让水,小伙子只是哼哼。爹看不上,恨改娃那份热情,敲着镰把嚷:“显人!疯前疯后的,还顾得干活!”改娃根本不吃这一套,腾地窜到拖拉机前头,拦住说:“我今儿偏让你喝这碗水!不喝,把机器开走!”小五傻愣愣地刹了车.脸同身上的汗衫一样红。半天,苦笑着,拿眼瞟着发怒的老头子.低着头,把一碗糖水咕嘟嘟灌下去。直到收工,他的头都没有抬起来。改娃像一个胜利者,谁也不看,大手大脚风快地下活,一眨眼便捆起一趟麦个子,爹被她甩得远远的。她站在地头,擦着汗,得意地拿手绢扇凉,还轻轻哼歌儿。待爹直着腰,瞪大眼盯她的时候,她又像没事一样,背身虎虎地扎新趟子了。那逗气的脸,那脸上奇怪地梗起的肉,使香雨的心灼痛。改娃长大了。她静静地想。她的脾气什么时候变得这样乖张.叫人不可捉摸,她没留意过。在她脑海里,改娃永远是个穿着不合身的大褂子、拖着一双裂口子鞋、翘着粗硬的小辫、捧着大碗、眼巴巴望桌上饭菜的小丫头。长大起来,又总见她在村路上疯、跑.书包在手上转圈甩,像风车。做活也忙忙的,碰得锅碗瓢勺叮当响。麦子运完后,她终于同爹吵了一架。爹说,晚上用电。她偏说.还用小五的机器。小五嘟嘟嚷嚷说:“机器晚上我们自己也要打麦。”改娃不等他说完,拿手挥掉他头上的草帽:“对你狗哥说,机器我先用!个把钟头,耽误你们了?”爹就同她吵。两人谁也不让,跳着脚.拍着腿。最后,改娃转过脸逼着小五:“你说,你今晚来不来!”小五有些怯,闪烁其词地说:“我三哥说,他后半夜米。”改娃有半分钟没有说话,死死盯着小五的脸,愤愤地说:“窝囊废!算了,我不管。……t”吃过晚饭.她就洗了脚,擦了澡,关门睡觉。金成不知什么时候溜了,等到爹妈四处找,已经没有踪影。奶奶愤愤地说:“尽吃柿子拣软的捏,雨雨干了一天.手打了泡,以后咋掂笔写字!那人高马大的,躺在屋里睡,你们都哑巴了,舍不得吵一声!你们呀……”香雨截断奶奶的话,不让她说。爹真够难的。他们在小刘庄是外姓.亲戚本家少.劳力弱,好不容易凑够十几个人,大家喝了两瓶白干酒.上了场,却坐在这里等电。爹心里什么滋味!电还没有来,大家坐在场上焦急地等着。“熊!还不是潘大头提成没弄到手,这会儿拿一手。”黑暗里。是谁骂骂咧唰嚷了一句。潘大头是大队电工,在小刘庄有几家亲戚。所以,大家都不接腔。夜色重归于寂静,蚯蚓在场边洼地里叫,不绝如缕,好像一根细细的游丝,一直攀绕到人们心里。在学校,该响熄灯铃了。那是县城新建的一所中学。是个偏僻的县城。香雨的同学们几乎没人分到这样糟的地方。她是历史系拔尖的学生,却看着成绩平平的同学留校,进社会科学院,到编辑部.她是憋一口气到这鬼地方来的。人生的第一个不公平带给她更大的狠劲。没有关系,就靠自个儿,哪里都一样。反正我要考研究生,有真才实学总会出人头地。可是现在……真是累极了,身心交瘁!一种幻灭感使她的意志崩溃。……她翻转身.仰面躺着。月亮还没出,也看不到星星,天字像一泓深不可测的大湖,灰黝黝的.压在她脸上。手臂碰上身旁的石磙,冰凉冰凉。……她是赌气请假回来的。校长微笑着说:“要请人代课。超过十天得扣工资。”“那你就扣吧!”她生硬地说。校长仍然笑着:“还是尽量赶回来,啊?”“要是赶不回来呢?”“……那你再来信。”——他真是宽宏大量.丝毫不计较头天吵过架。她是那样凶地同他吵,哭着,诉着,很有些像改娃。……天色很阴沉。好像有一堆流云在浮动。会不会下雨呢?他们没顾上听县广播站的天气预报。——也许广播线断了,门头上的喇叭根本就没响。……那个县的广播站她是去过的。很小的单位.两排土瓦房。他住在西头。中文系毕业。早她一年。人挺好,有些平庸,窝窝囊囊。干那么个小广播站的小编辑很当一回事,胸无大志。她觉得自己迟早会调到省城或别的地方,他会成为绊脚索,所以,她对他不冷不热,似乎没有什么爱情冲动。这次她没有考取研究生.也许他会私下里感到高兴。……石磙太凉,她把手收回到胸口上。不知怎么的,突然觉得自己在这世界上很孤独。无论在闭塞的学校,还是在偏远的小村,她都孤零零的,没有一个知音。她二十六岁了,不知道怎样在人海里穿过来,对谁也不曾留意。心像右磙一样冷,也像石磙一样坚硬执著,一味要压平面前的路。她知道,他会来信的。这时候.她有点希望收到一封不拘谁的信,但却不敢指望谁能解除她的忧烦。她对遥远的她所工作和生括的那个环境充满厌恶,宁可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麦场上。……天是越来越阴了,凉气变成微风,麦垛上的枯叶发出簌簌的响声。但愿不要下雨,今夜和明天都不要下。她这样盯着天空看着,大渐渐升高.升高,高到一无所有……(未完待续)
治疗白癜风的秘方白癜风哪家医院看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