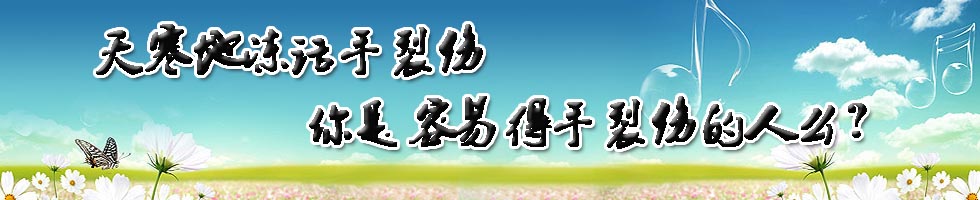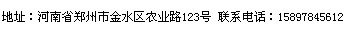一个画画出身的编舞家,编出了程序员最爱的
水母小星球通信
我的作品都是和人的灵魂有关系的,是和人的灵魂和思想的沟通与交流。我们以一种坦诚的表达方式,让观众觉得好像在看自己的日记一样。
年,当沈伟第一次带着自己的舞作《春之祭》和《天梯》回到中国与观众见面时,他曾经这样抽象概括自己的作品。
试图用一两句话描述沈伟的作品是徒劳的。
欧洲批评家说:沈伟的作品不能叫现代舞,也不能叫传统舞,应该就叫舞蹈,因为它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而仅仅用“舞蹈”来描绘沈伟的作品似乎也过于局限。
年年底,沈伟在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ParkAvenueArmory)上演媒体视觉表演《分与合》(UndividedDivided)。
军械库平方米的大厅,演出区域铺了大面积的屏幕,大量应用声音、影像、现场装置、行动绘画,观众可自由出入。
年年底在香港文化中心首演的《荧》,则用一块斜坡状平板、舞者的身体和颜料,现场绘制成了一幅抽象画。
今年10月5日,他受BAM委约创作的最新作品《亦非此彼》(Neither)刚刚在纽约上演。在这部作品里,沈伟把萨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与美国后现代派作曲家莫顿·费尔德曼(MortonFeldman)合作的独唱歌剧改编成了舞蹈。
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有绘画、有装置、有多媒体艺术,甚至还有观众的参与。沈伟是编舞,也是布景、舞台、服装的设计。因而有媒体评价,沈伟的作品是舞蹈,又不仅仅是舞蹈——它是所有视觉和艺术表达的总和。
从某种程度上说,沈伟难以定义的作品创作来自自己复杂的身份和经历。
出身于湖南一个戏曲世家,沈伟练过戏曲,也学过油画,虽然没有系统学过舞蹈,但对身体和舞动抱有很大的兴趣。
年,为了块的奖金,沈伟参加了在当地的一个舞蹈比赛。凭借自己编的一支舞,他如愿拿到了大奖。比赛的评委老师建议他去广州学舞。后来他成为那个现代舞班的插班生,和金星、王玫是同学,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学现代舞的人。
从广州到纽约,舞蹈成为沈伟被世界认识的途径,而他却从没放弃过绘画。他的画作在纽约和香港举办过个展。沈伟现代舞团的一位舞者曾经表述,与其说沈伟在编舞,不如说沈伟在用舞者进行绘画。
纽约前波画廊的老板茅为清(ChristopherMao)曾经这样评价绘画对于沈伟的意义:
“许多人都弄反了沈伟的成就的顺序,固然,他作为舞者和编舞家而成名,然而,从他年的《声希》和《天梯》开始,视觉艺术就一直在他的编舞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他从童年开始对绘画的兴趣就常常超过舞蹈和音乐。对很多国内的艺术爱好者来说,《声希》、《天梯》和《春之祭》一起,也许是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画卷”之外,沈伟最为人熟悉的舞蹈作品。
《声希》是沈伟早期的作品,取意于《道德经》“大音希声”,沈伟希望这一作品表达“谦逊、真理和诚挚的冥思”。而作品的英文名“folding”似乎更能透露这个作品的动作形态。
在创作这一作品之时,沈伟着迷于各种物体以及人体折叠的形态,希望由这种简单的动作发展出另一个时空。
舞台的后侧挂着八大山人的游鱼画作,在约翰·塔弗纳《圣母最后的安眠》和藏僧吟经声中,舞者们以难以觉察的舞步在台上缓缓游移。他们白面、高髻,仿佛奇异的外星人。他们以赤色或红黑相间的长裙曳地而行,慢慢俯身、低头。
在一些时刻,观众的视线被舞者的长裙遮蔽,两个舞者彼此紧贴缓慢行动,仿佛从同一副躯干中长出了不同的头颅和四肢。比起舞蹈,以慢和静为特征的《声希》更像是一个运动的装置作品。
《天梯》是沈伟现代舞团的建团的作品,在沈伟的描述中,这部舞作“风格与超现实主义很接近”。
我开始对简单的中心控制的动作与空间、时间和视觉元素之间的关系做细致的工作。在研究《声希》开启的运动概念的同时,也在研究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保罗·德尔沃(PaulDelvaux)的画作,这些画作最终成为《天梯》灵感的源泉。一个宽阔的古典主义大台阶横亘在舞台之上。舞者赤裸上身,下身穿着飘逸的长裙和裤子,在阿尔沃·帕尔特的极简主义音乐缓缓移动。空灵、洁白、一尘不染、未来感……这些词构成了《天梯》演出之后的大部分评论。
年,沈伟将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改头换面重排。一反《声希》和《天梯》的缓慢与写意,这一在国际上声名大噪的作品,充满了能量爆发般的不规则运用。
黑灰色的斑驳舞台,白色纵横的交错线条划分了地面空间,舞者跟着土耳其钢琴家法佐·塞依(FazilSay)改编的四手联弹版《春之祭》音乐跑动、跳跃,仿佛坠落在扭曲棋盘上的12颗棋子。没有了少女与献祭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快速动作。
不同于尼金斯基的芭蕾舞版,也不同于后来玛莎葛·兰姆、皮娜·鲍什等著名的改编版本,沈伟在年创作的《春之祭》完全抛开了音乐中的故事性,韵律和身体交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一个一百年前的音乐,现在来编舞,价值和必要性在哪里?是音乐重新做一次,还是舞蹈重新排一次?在不断自我询问之后,沈伟拿出了自己的答案。
“《春之祭》在一百年前革新了作曲方式,影响了整个现代音乐的发展——这是它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艺术家,沈伟选择用一种新的运动方式和身体表现方式,与音乐作曲方式的革新相互对应。
“在创作时,阐述和用身体的方式是非常科学的,这是我非常重要的艺术表达。沈伟用“自然身体发展”描述自己作品中的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在《地图》中更为系统清晰。同样是是灰黑的地板,同样是散落于地图之上的人体棋子,从视觉上,年纽约林肯中心委约创作的《地图》似乎是《春之祭》的延续。然而,沈伟在《地图》中的比《春之祭》更进一步。
用沈伟自己的话说,这个作品“野心很大”——他想让所有的动作都来自自己的理论,而且这些动作不是编出来的,而是自然带出来的。
沈伟选择了斯蒂夫·瑞奇(SteveRage)的《沙漠音乐》。比起《春之祭》,斯蒂夫·瑞奇的当代作曲法更现代,沈伟也选择了更让人眼花缭乱的运动方式。他研究了在关节处旋转的无数可能性、弹跳的所有形式,肢体的反弹和悬挂,以及从身体躯干产生的能量如何在四肢引发律动。
跟随着瑞奇音乐的脉动节奏,19名舞者在舞台上做着不同的动作,在节拍切割下,舞者之间的呼吸和动作相互切换,最后在舞台上呈现出一个万花筒一般的地图。
这部作品被沈伟称之为“动作上下了最大的功夫”,同时也是最考验舞者的一个作品,逼近每一个舞者的身体极限。
让沈伟觉得格外有趣的是,这部作品在美国演出之后,格外受到程序员、理工科出身的人的喜爱。
“也许因为在其中每一拍和空间的分工都非常精确,像是电脑做出来,却又是完全自然。对他来说,理性的计算和感性的艺术,从来不是一对反义词。
“我的逻辑思维是非常强的——但是这和做艺术并不矛盾,艺术在感官上非常重要,但是不一定非要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