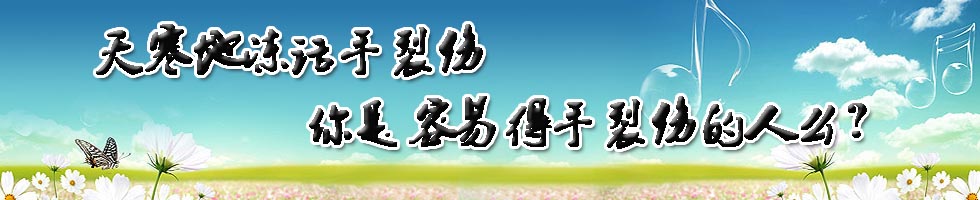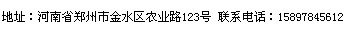华语独立裁公道易,裁人心难
《箭士柳白猿》是徐浩峰第二部导演作品,也可能是他迄今最好的作品。
之所以这么说,在于第一部《倭寇的踪迹》处在徐浩峰的实验探索阶段,电影视听、剪辑方面尚不成熟,而第三部《师父》叙事练达,强调故事的推进,但在相当高的完成度上少了一种东方的神韵。
介于二者之间的《箭士柳白猿》,不但以一种形散神聚的结构拍摄出属于东方的诗情画意之美,而且在主题上超越另外两部,透过武者的悲哀,展现人生的缺憾与宿命色彩。
可以说,徐氏风格在小众影迷圈里已经广为人知,他凭借一己之力革新了功夫片的格局,缔造了一种讲求武打原理,追求写实效果的打斗场面,并且展现了银幕上少见的传统械斗——《倭寇的踪迹》里的戚家刀,《箭士柳白猿》中的中式古典弓、《师父》里的八斩刀,弥补了银幕上对传统兵器呈现的缺乏,更进一步,他为人们呈现了逝去的武林,晚清、民国武行的兴衰。
在此意义上,徐浩峰的影片已不再是传统的武侠片,而是有了另一种界定,即武道片,或者武行片。武术中的原理、武术与人心的关系成为其故事的内核,而武行、武馆这一营生的行当成为其故事的载体。
具体到《箭士柳白猿》,影片讲述了民国军阀混战之下,一个叫双喜的人因目睹姐姐遭地主强暴,在庙中留下纸人,跳出墙头,意外救助了当时的武林仲裁人柳白猿,于是得以学成箭术,成为新一代柳白猿的故事。
柳白猿作为一个名号,管的是武行的冲突,代表的是公道,不能夹杂私情。如果说《倭寇的踪迹》、《师父》讲的是规矩——武行的规矩、做人的规矩,那么《箭士柳白猿》讲述的便是武行的仲裁、人心的仲裁。
关于武行,《箭士柳白猿》中展现了一种少见的踢馆比武方式“划拉巴子”,展现了长枪的打法,包括赵峥临时练就的赵子龙十八枪、于承惠老师的岳武穆十三枪,展现了混血女人二冬的绳法,以及宋洋学就的中式古典弓射法。
其中最为精到的原理呈现,便是上一代柳白猿教射箭的经过,步步为营,层层推进,展现武术与人心的关系。这一部分虽然猎奇,但却是人物必不可少的铺垫。箭术的完成,意指柳白猿身份的确立,这一身份要求心定、公道。
导演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打破这种心定、公道,放置角色于心乱、私情之中。柳白猿面对的,一是混血女人二冬及军阀过德诚,另一是名伶月牙红及匡一民。几人各怀鬼胎与柳白猿产生交集。二冬想借柳白猿之手除掉杀父仇人杨乃兴,柳白猿帮忙,却发现被杨乃兴的师父匡一民从气势上镇住。
在帮忙期间,柳白猿结实了名伶月牙红,月牙红以身相许触动柳白猿,私情大发,正打算放弃柳白猿的身份,却发现这又是一个圈套,一切都是匡一民一手安排,为的是揭开他的真实身份。
在这些看似散乱勾连、旁敲侧击的情节之下,聚拢到一起的精神便是呈现每个角色对内心的难以仲裁。二冬借柳白猿杀父不成,心属意于柳白猿而不得回应,柳白猿为二冬做所,都体现了身为武林仲裁人的一面,公道、守心。
名伶月牙红却动了柳白猿的内心,水果店只要“15个苹果”以身相许,更是让柳白猿放弃了身份,但殊不知这是另一场圈套,月牙红最终依旧委身于匡一民,随其远去。
军阀过德诚想除掉“下野”的杨乃兴,但被师父匡一民阻拦,在两人的枪法大战中败下阵来。辅佐杨乃兴的匡一民大志难成,只能企盼杨乃兴东山再起。
而影片的一号主角柳白猿,在姐姐被强暴而无能为力的阴影下,走上仲裁人之路,心定也在纷乱时局和个人情欲之下出现动摇。
乱世之下,人人皆有其使命,但这使命却变成了宿命。结尾塔林大战,上演枪与箭的对决,匡一民的枪代表着向外的事业,柳白猿的箭代表着向内的内心,在一片佛教塔林之间,角色的比武恰似隐喻人的内在与外在的博弈。
这是他们求的一场比武,缅怀逝去的传统与道义,但外在决斗停而内心决斗不止,四人继续困于自己的宿命,匡一民继续寻人辅佐,月牙红尾随其而去,二冬“看一眼”心上人而再不相见,柳白猿端箭凝视画的头像,继续这一身份的使命。各色人等,囿于宿命,难仲心裁。
徐浩峰曾说,他认为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讲认输的,都是表现人生的缺憾。在此意义上,《箭士柳白猿》无疑成了一次完美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