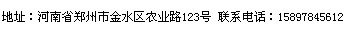塞萨尔巴列霍诗选
塞萨尔?巴列霍(——),秘鲁诗人,生于圣地亚哥,逝世于法国巴黎,他的作品是二十世纪西班牙语诗坛的巅峰之一。
判决
我出生的那一天
神正好生病
每个人都知道我活着,
知道我是坏蛋;而他们不知道
那年一月里的十二月。
因为我出生的那一天
神正好生病。
在我形而上的空中
有一个洞
没有人会察觉到:
以火光之花说话的
寂静的修道院。
我出生的那一天
神正好生病。
听着,兄弟,听着……
就这样。但不要叫我离去
而不带着十二月。
不丢掉一月。
因为我出生的那一天
神正好生病。
每个人都知道我活着,
知道我嚼烟草……而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在我的诗里柩车的
黑烟吱吱作响
焦燥的风──
自史芬克斯──沙漠中的探问者
身上展开。
每个人都知道……而他们不知道
光患了痨病
而荫影痴肥……
并且他们不知道神秘会合成……
或者谁是那悲伤而声音美妙的
驼峰,自远处宣示
从界限到界限的子午圈的脚步。
我出生的那一天
神病得
很厉害。
(陈黎、张芬龄译)
我们的爸妈
我们的爸妈
他们几时会回来呢?
盲眼的桑第雅哥钟正敲六下
并且天已经很黑了。
妈妈说他不会去久的。
阿桂提达,纳第瓦,迷古,
小心你们要去的地方,那儿
叠影的幽灵出没
当当弹响他们的记忆走向
寂静的天井,那儿
母鸡仍惊魂未定,
她们吓得这么厉害呢。
最好就留在这儿,
妈妈说她不会去久的。
不要再烦躁不安了。去看看
我们的船。我的是最漂亮的了,
我们成天玩的那几只,
不必争吵,事实是如此:
它们仍然在池塘里,载着它们的
糖果,准备明天出航。
让我们就这样等着,乖乖的,
别无选择的,等
爸妈回来,等他们的赔偿──
总是在门口,总是
把我们留在家里
彷佛我们不会
跟着走开。
阿桂提达,纳第瓦,迷古?
我叫着,在黑暗中摸索我的路。
他们不能留下我一个人,
我不可能是那惟一的囚犯。
(陈黎、张芬龄译)
我明天穿的衣服
我明天穿的衣服
我的洗衣妇还没有替我洗好:
一度她在她欧蒂莉亚的血脉里洗它,
在她心的喷泉里,而今天
我最好不要想知道 我是否让
我的衣服被不义的行为弄脏。
如今既然没有人到水边去,
整刷羽毛的亚布遂僵硬于
我的刺绣样本,而所有摆在夜桌上
原本会属于我的东西──
就在我的身边──
却不是我的了。
它们还是她的财产,
被她麦般的善良安抚,情同手足。
而只要让我知道她会不会回来;
而只要让我知道她会在哪一个明天走进来
递给我洗好的衣服,我心灵的
洗衣妇。在哪一个明天,她会满意地走进来
带着成果,绽开笑容,高兴她
证实自己的确知道,的确能够
一付她为什么不能的样子!
把所有的混乱弄蓝并且烫平。
(陈黎、张芬龄译)
我想到你的性
我想到你的性。
我的心跟着简单了。我想到你的性,
在白日成型的婴儿之前。
我触到快乐的花蕾,正是盛开时节。
而一个古老的感情死了,
在脑子里腐烂。
我想到你的性,一个比荫影的子宫
更多产而悦耳的犁沟,
纵使死亡是由上帝亲自授胎
生产。
哦良心,
我想到(是真的)自由自在的野兽
它享受它想要的、能找到的一切。
哦,夕暮甜蜜的绯闻。
哦无声的喧闹。
闹喧的声无!
(陈黎、张芬龄译)
在我们同睡过许多夜晚的
在我们同睡过许多夜晚的
那个角落,我现在坐下来等着
再走。死去的恋人们的床
被拿开,或者另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往为别的事你会早早来到
而现在未见你出现。就在这个角落
有一夜我依在你身边读书,
在你温柔的乳间,
读一篇都德的小说。这是我们钟爱的
角落。请不要记错。
我开始回忆那些失去的
夏日时光,你的来临,你的离去
短暂,满足,苍白地穿过那些房间。
在这个潮湿的夜里,
如今离我们两人都远远地,我猛然跃起……
那是两扇开阖的门,
两扇在风中来来去去的门
阴影 对 阴影
(陈黎、张芬龄译)
哦小囚室的四面墙
哦小囚室的四面墙。
啊四面惨白的墙
丝毫无误地对着同样一个数字。
神经的繁殖地,邪恶的裂口。
你如何在你的四个角落之间
扭拧你每日上炼的四肢。
带着无数钥匙的慈爱的监护人啊,
如果你在这儿,如果你能知道
到什么时候这些墙还一直是四面就好了。
我们就会合起来对抗它们,我们两个,
永远要多出两个。而你不会哭泣,
你会吗,我的救星!
哦小囚室的墙。
长的两面最叫我痛苦,
彷佛两个死去的母亲,在黑暗中
各自牵着孩子的手
穿过梦幻的
下倾斜面。
而我孤单地留在这儿,
右手高高地搜寻着
第三只手,来
护养,在我的何处与何时之间,
这个无用的成人期。
(陈黎、张芬龄译)
你如何追猎我们……
你如何追猎我们,哦抖动着教条般
卷册的海啊。如何痛苦而巨大啊
你在发烧的日头的巢窟里。
你用你的手斧攻击我们,
你用你的刀刃攻击我们,
在疯狂的芝麻里乱砍、乱砍,
当波浪哭泣地翻身,在
漏下四方之风以及
所有的大事记录之后,千万只饰边曲折的
钨的大浅盘,犬齿般的收缩,
以及狂喜龟类的L字。
跟着白日的肩膀胆怯的颤抖
颤动着的黑翼的哲学。
海,确定的版本,
在它单一的书页上反面
对着正面。
(陈黎、张芬龄译)
雨雹下得这么大,彷佛我应该记起
雨雹下得这么大,彷佛我应该记起
并且添加我从
每一个风暴喷口搜集来的
珍珠。
这场雨千万不要干去。
除非如今我能够为她
落下,或者被埋葬
深浸于自每一处火迸射
过来的水里。
这场雨会带给我多少东西呢?
我怕我还有一边腰干着;
我怕它会猝然停止,留下我生疏地
在不可信的声带的干旱里,
在那上面,
为了带来协和
你必须一直升起,不能降下!
我们不是往下升吗?
唱吧,雨啊,在仍然没有海的岸上!
(陈黎、张芬龄译)
我在笑
一个小圆石,只一个,最底下的一个,
控制了
整座预感不吉、法老似的沙丘。
大气有了记忆与渴望的紧张
而在阳光下静静地坠落
直到它向金字塔坚持要它们的颈子。
渴。流浪的部落水化物的忧郁,
一滴
接
一滴,
从世纪到分钟。
有三个平行的三,
留着太古胡须的人
行进着 3 3 3
这通告是伟大鞋店的时代,
是赤脚行进的时代
从死亡 朝向 死亡。
(陈黎、张芬龄译)
九只怪物
而不幸地,
痛苦时时刻刻在这个世界滋长着,
以每秒三十分钟的速度,一步一步地。
而痛苦的本质是两次的痛苦
而殉难的境况,食肉的、狼吞虎咽的,
是两次的痛苦
而最纯净的草地它的功用是两次的
痛苦
而存在的好处,是双倍的加害我们。
从来,人类之人啊
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痛苦在胸间,在衣领,在钱包,
在玻璃杯,在屠宰摊,在算术里!
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痛苦的感情,
远方从来不曾威胁得这么近,
火从来不曾如此逼真地扮演它
死火的角色!
从来,健康大臣啊,从来不曾见过
更致命的健康
不曾见过偏头痛从额头榨出这么多额头!
而家俱在它的抽屉里装着的是,痛苦,
心在它的抽屉里,痛苦
蜥蝪在它的抽屉里,痛苦。
困厄滋长着,兄弟啊,
比引擎还快,以十具引擎的速度,跟着
卢梭的家畜,跟着我们的面包;
邪恶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滋长蔓延着
它是一场自生的洪水
带着它自己的泥土、自己的固体云。
苦难颠倒位置,以一种
叫水质的幽默垂直站立着的
函数,
眼睛被看到而这只耳朵,被听到,
而这只耳朵在放电的时刻敲了九下
丧钟,九阵哄笑
在麦的时刻,以及九声女音
在哭泣的时刻,以及九篇颂歌
在饥饿的时刻,以及九声霹雳
九声鞭响,减掉一声吶喊。
痛苦抓着我们,兄弟啊,
从背后,从侧面,
逼我们疯狂摄入电影,
将我们钉进留声机,
将我们拔开放到床里,垂直地掉进
我们的车票,我们的信;
苦难重且大,你可以祈祷……
因为痛苦的缘故
有一些人
被生出,一些人长大,一些人死去,
而另有一些人生出来但没有死,另有一些人
既不曾生也不曾死(这是最多的)。
并且因为苦难的
缘故,我从头到脚
充满哀伤
看到面包被钉死于十字架,萝卜
流着血,
洋葱哭泣,
谷类率皆成为面粉,
盐巴磨剩粉末,水逃开
酒成为戴荆冕的耶稣像,
雪如此苍白,而阳光如此被烧焦!
如何,人类的兄弟啊,
如何能不告诉你我已经无法再
我已经无法再能够忍受这么多的抽屉,
这么多的分钟,这么多的
蜥蝪以及这么多的
倒错,这么多的距离,这么饥渴的饥渴!
健康大臣啊:要怎么办呢?
不幸地,人类之人,
兄弟啊,要办的东西太多了!
(陈黎、张芬龄译)
饥饿者的刑轮
我发着臭气,穿出自己的牙缝,
咆哮,推进,
挤落了我的裤子……
我的胃空出,我的小肠空出,
贫乏把我从自己的牙缝间拖出,
我的袖口被一支牙签钩住。
谁有一块石头
可以让我现在坐上去?
即使是那块绊倒刚生产过的女人的石头,
羔羊的母亲,缘由,根源,
有没有这么一块石头?
至少那另一块畏缩地
钻进我灵魂的石头!
至少
刺马钉,或者那坏掉的(谦卑的海洋),
或者甚至你不屑于用来丢人的一块,
把它给我吧!
要不然那块在一场羞辱中孤独且被戮刺的石头
把那块给我吧!
即使是扭曲、加冠了的一块,在那上头
正直良知的脚步只一度回响,
或者,如果没有其它的石头,就给我们那块以优美弧度拋出,
即将自动落下,
以道地的内脏自居的,
把它给我吧!
难道没有人能够给我一块面包吗?
我将不再是一向的我了,
只求给我
一块石头坐下,
只求给我
(拜托你们!)一块面包坐下,
只求给我
用西班牙语
某样终于可以喝,可以吃,可以活,可以休息的东西,
然后我就会走开……
我发现到一个陌生的形体,我的衬衫
褴褛而邋遢
我什么也没有了,真可怕哪。
(陈黎、张芬龄译)
乞丐们
乞丐们为西班牙战斗
在巴黎行乞,在罗马,在布拉格
并因此,经由哀求、未开化的手,
鉴证了使徒们的脚,在伦敦,在纽约,在墨西哥。
他们参加了一份,向上帝苦苦
要求圣丹德尔,
一场迄今无人败过的竞赛。
他们把自己投献给古老的
苦难,他们怒吼,对个体哭出
群体的枪弹,
以呻吟攻击,
以单纯的行乞杀敌。
一个步兵的祈求──
他们的武器沿着金属向上祈求,
他的愤怒祈求,比凶恶的火药更能命中要害。
沉默的中队,他们以
致命的节奏发射他们的温驯
从门口,从他们自身,啊从他们自身。
潜在的战士,
将雷声的蹄铁钉上他们赤裸的脚跟,
邪恶的,数字的,
拖着他们惯用的名字,
面包屑在臀部,
一枝双管的来复枪:血以及血。
诗人向武装的苦难致敬!
注:圣丹德尔,西班牙北部之港城,附近曾发现史前期洞穴,上有壁画。
(陈黎、张芬龄译)
给一位共和军英雄的小祈祷文
一本书长留在他死去的腰际,
一本书自他死去的身体萌芽。
他们带走了英雄,
而他有血有肉而不幸的嘴巴进入我们的呼吸;
我们汗流浃背,在我们肚脐的重担之下;
流浪的月亮跟随我们;
死者,同样地,也因悲伤流汗。
而一本书,在托雷铎战场,
一本书,在其上,在其下,一本书自他的身体萌芽。
紫色的颊骨的诗集,在说与
未说之间,
用伴随着他的心与道德讯息写成的
诗集。
书留下,其它什么也没有,因为坟墓里
一只昆虫也没有,
而沾血的空气留在他的袖边
逐渐虚化,没入永恒。
我们汗流浃背,在我们肚脐的重担之下,
死者,同样地,也因悲伤流汗
而一本书,我感动地看到,
一本书,在其上,在其下
一本书猛烈地自他的身体萌芽。
(陈黎、张芬龄译)
群体
战事完毕,
战斗者死去,一个人走向前
对他说:“不要死啊,我这么爱你!”
但死去的身体,唉,仍然死去。
另外两个人走过去,他们也说:
“不要离开我们!勇敢活过来啊!”
但死去的身体,唉,仍然死去。
二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五十万个人跑到他身旁,
大叫:“这么多的爱,而没有半点法子对付死!”
但死去的身体,唉,仍然死去。
成百万的人围绕在他身边,
众口一词的请求:“留在这儿啊,兄弟!”
但死去的身体,唉,仍然死去。
然后全世界的人
都围绕在他的身边,悲伤的尸体感动地看着他们:
他缓缓起身,
拥抱过第一个人;开始走动……
(陈黎、张芬龄译)
西班牙,从我这儿把这个杯子拿去
世界的孩子们
如果西班牙垮了──我是说如果──
如果她从天上
垮了下来,让两张地上的岩床
像吊腕带一样抓住她的手臂;
孩子们,那些凹洼的庙宇是怎么样的年代啊!
在阳光中我传给你的讯息多么早啊!
在你胸中原始的吵声多么急速啊!
在练习本里你的数字2有多么古老啊!
世界的孩子们,妈妈西班牙
她辛苦地挺着肚子;
她是手持藤条的我们的老师,
是妈妈兼老师,
十字架兼木头,因为她给你高度,
晕眩,除法,加法,孩子们;
饶舌的父母们,是她在照顾一切啊!
如果她垮了──我是说如果──如果西班牙
从地上垮了下来
他们将如何停止长大,孩子们!
如何年岁将责罚它的月份!
如何牙齿将十颗十颗地串在一起,
双元音化做钢笔的笔划,流泪的勋章!
如何年幼的羔羊它的腿
将继续被巨大的墨水池所绑着!
如何你们将走下字母的阶梯
到达悲伤所生自的字母!
孩子们,
斗士的子孙,暂时
压低你们的声音,因为此刻西班牙正在
动物的王国里分发生命力,
小花、流星,还有人哪,
压低你们的声音,因为她深浸在
她伟大的强热里,不知道该
做些什么,而在她的手中
头颅在说话,滔滔不绝地说着说着,
头颅,有发辫的头颅!
头颅,充满活力的头颅!
压低你们的声音,我告诉你们:
静下你们的声音,音节的歌唱,事物的
哭泣以及金字塔微弱的耳语,啊甚至静下
被两颗石头压着的你们太阳穴的呻吟!
压低你们的呼吸,并且如果
她的手臂掉下来,
如果她的藤条咻咻地鞭打,如果夜已降临,
如果天空在两片地狱的边缘地区间找到它的位置,
如果那些门的声音喧哗起来,
如果我来迟了,
如果你看不到任何人,如果钝的铅笔
吓倒了你们,如果妈妈
西班牙垮了──我是说如果──
快出去,世界的孩子们,快出去找她啊……
(陈黎、张芬龄译)
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
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把一个男孩捣碎成同样多的鸟儿,把鸟儿捣碎成一个个小蛋;穷人的愤怒拥有一瓶油去对抗两瓶醋.愤怒把一棵树捣碎成一片片叶子,把叶子捣碎成大小不同的芽,把芽捣碎成一条条清晰的沟;穷人的愤怒拥有两条河去对抗很多大海.愤怒把好人捣碎成各种怀疑,把怀疑捣碎成三个相同的弧,再把弧捣碎成难以想像的坟墓;穷人的愤怒拥有一块铁去对付两把匕首愤怒把灵魂捣碎成很多肉体,把肉体捣碎成不同的器官,再把器官捣碎成八度音的思想;穷人的愤怒拥有一把烈火去对抗两个火山口.
饥饿的轮子
我从自己的牙齿之间出来冒着烟,
叫喊着,推搡着,
脱着裤子……
倒空我的胃,倒空我的肠,
贫穷把我从我自己的牙齿间拽出来,
用一根小棍勾在衬衣袖口。
一块可以坐上去的石头
现在也不给我?
那块曾绊倒分娩的女人,
羊羔,原因,根脉的母亲,
现在也不给我?
至少那一块,
它经过的时候曾向我的灵魂弯腰!
至少
那块石灰质的或者邪恶的(卑贱的海洋)
或者没用的都不能掷向人的,
现在就给我!
那一块孤零零横在一声辱骂里的,
现在就给我!
那一块扭曲的压顶的,只回响过
一次正直的意念运行,
或者,至少,另一块,扔出去有庄严的弧线,
能落在自己上面,
充当真正的内脏,
现在就给我!
一块面包,现在也不能给我?
我一直坚持的已经不再坚持,
但是给我,
一块可以坐上去的石头,
但是给我
劳驾,一块可以坐上去的面包,
但是给我,
用西班牙语
一点儿,总之,可喝的,可吃的,可活的,可歇息的,
然后我就走……
我成了奇怪的模样,我的衬衣
很破很脏
我已经一无所有,这很吓人。
骨骼点名册
他们高声呼喝:
“命令他同时举起双手。”
可是那不可能。
“命令他们在他哭的时候量他的步幅。”
可是那不可能。
“命令他在零字没有用的时候想固定的思想。”
可是那不可能。
“命令他做疯狂的事。”
可是那不可能。
“在他和另一个跟他一样的人之间安置一群跟他一样的人。”
可是那不可能。
“命令他们拿他跟他自己比较。”
可是那不可能。
“那么,命令他们用他的名字唤他。”
可是那不可能。
良知
“哎,妈妈,世上有一个地方叫巴黎。是个大地方,很远,真的很大。”
母亲替我翻起外衣领子,不是因为下雪,是为了让雪开始下。
父亲的妻子爱我。她后退的时候向着我的诞生,前进的时候向着我的死亡。因为我双重属于她,其一是离家,其二是回家。我一回到家里,她就关起来了。这就是她的眼睛给我那么多的缘故,她的眼睛里只有我,她出现在完成了的工作里,在履行了的承诺里,跟我一起。
母亲是为我忏悔么?是由我命名么?她给我其他的兄弟为什么比我少?比方说,维克多吧,他已经那么老了,人们甚至说:“他看起来像他父亲的弟弟!”大概因为我常常出门!大概因为我见世面多些!
母亲为我的回归故事添加色彩。面对着有我在家的生活,想起我在她体内历经两个心脏的旅行,当我在讨论灵魂的时候说“那个晚上我很快乐”的时候,她就羞愧起来,脸色变成灰白。可是她悲哀的时候更多,她很容易悲哀。
“儿子,你多么老了!?”
她大步走过黄的颜色去哭,因为她从我脸上的伤口和剑刃看出我老了。她为我哭,为我悲哀。既然我永远是她的儿子,为什么要我年轻呢?为什么世上的母亲觉得独生子老了就伤心呢?反正他们的年纪永远赶不上她们?为什么儿子的年纪越大就越接近父亲呢?我的母亲哭,是因为我在我的年纪衰老而等不到她那个年纪才衰老。
在她的生命里,我的离家点比归家点更接近表面。由于回家的严格时间限制,我像母亲的当家男人更多于像母亲的儿子。这里面有一种纯真,今天用三朵火照亮我们。从此,我就反反复复说同样的话,直至终于无话可说:
“哎,妈妈,世上有一个地方叫巴黎。是个大地方,很远,真的很大。”
父亲的妻子一边吃午饭,一边听我说话,她那双终于不免于死的眼睛,沿着我的臂膀温柔地向下移动。
时间的暴力
都死了。
多妮亚·安多尼奥死了,在村子里卖廉价面包的那个声音沙哑的女人。
圣地亚哥神父死了,他喜欢年轻的男男女女跟他打招呼,不管是谁,一概回应:“你好,霍西!你好,玛丽亚!”
年轻的金发女子卡利奥塔死了,留下一个婴孩,母亲死后八天也死了。
阿尔比纳姑姑死了,她常常吟诵传统的时态和语式,在走廊里为受人敬重的女官员伊莎多拉缝衣服。
一个瞎掉一只眼睛的老人死了,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他早上在阳光下面睡觉,在街角的洋铁厂门口抖尘。
拉约死了,跟我一样高的一条狗。不知道被什么人射杀。
姐夫鲁卡斯死了,愿他安息,在我经验里没有别人的下雨天,我就想起他。
母亲死了,在我的左轮手枪里,妹妹在我的拳头里,兄弟在我流血的内脏里,有一种悲哀中之悲哀把他们三个人连结在一起,在年复一年的八月份。
东师门德斯死了,高大的醉醺醺的,读着谱用单簧管吹哀怨的托卡塔,太阳下山之前,邻近的鸡老早就在那节奏里睡着了。
我的永恒也死了,我在为它守灵。
一生最危急的时刻
有人说:
“我一生最危急的时刻是在马恩河战役进行的时候,我胸部中了枪。”
另一个人说:
“我一生最危急的时刻是在横滨发生海啸的时候,我躲在一家漆器店的檐篷下面,奇迹地生还。”
又另一个人说:
“我一生最危急的时刻是在睡午觉的时候。”
又另一个人说:
“我一生最危急的时刻是在最孤独的时候。”
又另一个人说:
“我一生最危急的时刻是在秘鲁坐牢的时候。”
又另一个人说:
“我一生最危急的时刻是在从侧面吓倒父亲的时候。”
最后一个人说:
“我一生最危急的时刻还没到来。”
生命的发现
先生们,今天是我第一次谈论生命的存在。先生们,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享受生命中那种强烈、即时而且新鲜的感受,今天,这种感受第一次使我欢欣鼓舞,快乐到几乎要哭。
我快乐是因为从来不曾有过那种感受。我鼓舞是因为以前没有感觉到生命存在。从来没有感觉到。谁要是说我有,那是谎话。他说谎,而他的谎话伤透我的心。我的欢欣源出于对个人探索生命的信念,没有人能够动摇这个信念,谁想这样做,他的舌头就会跌出来,他的骨头也会跌出来,他必须跑来跑去捡,冒着捡错别人骨头的险,才能够在我眼前站立。
从来没有生命存在过,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人经过,直到今天。从来没有房屋、街道、空气和地平线,直到今天。如果我的朋友佩里埃特此刻到来,我会说不认识他,说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到底我是什么时候结识佩里埃特的呢?今天是我们初次交上朋友。我会让他走,然后再回来看我,好像不认得我一样,那是说,第一次。
今天,什么人,什么东西,我都不认得了。我发现自己处身于一个陌生的国度,一切都有与生俱来的玲珑浮凸,有主显节那种永不暗淡的光。不,先生,别跟那位绅士说话。你并不认识他,无聊的攀谈会让他惊讶。别把你的脚放在那石子上:谁知道它并不是石,你会整个人落空。你要当心,因为我们正处身于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我活过的时间是多么短呀!我的诞生是那么近的事,没有什么度量单位可以计算我的年纪。我是刚刚出生的啊!我还不曾开始生活呢!先生们:我这么小,几乎容不下一天。
我从来没有听过手推车的噪音,直到今天,它们运送石头去筑豪斯曼路。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跟春天并排着走,一边说:“假如死亡是另一个样子……”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见过圣心教堂圆顶上金黄的阳光。直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小孩走过来用他的嘴巴深深注视我。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不知道有一扇门、另一扇门和远处雄壮的歌声。
别管我!生命已经让我看透自己的死亡。
渴望停止了……
渴望停止了,尾巴向天。生命猛然截断自己。我的血溅在自己身上,流漓出女性的线条。甚至城市也跑出来查看是什么这样突然中断。
“男人的这个儿子发生什么事了?”城市高声叫喊,而在罗浮宫里,一个小孩看见另一个小孩的肖像就惊慌大哭起来。
“女人的这个儿子发生什么事了?”城市高声叫喊,而一座路德维希王朝时代雕像的掌心长出一茎青草。
渴望在举手所及的高处停止。而我不躲在自己背后窥看自己是否在下面走过或者在上面游荡。
有一个人变成残废
有一个人变成残废,不是在火线上而是在一次拥抱中,不在战争时期而在和平时期。他失去面孔是因为爱而不是因为憎恨。他在正常生活中而不是在遭遇意外时失去它。他在自然规律中而不是在人的动乱中失去它。比柯特上校,“残废退伍军人会”会长,被年的火药吃掉了嘴巴。我认识这个伤残人,他被不死的远古空气吃掉了面孔。
死面孔在活躯干上。僵硬的面孔被钉子镶在活的头上。这面孔变成头颅的后脑勺,头颅上的头。我有一次看见一棵树转背向我。另一次看见一条路转背向我。转背的树只生长在从来没有人诞生也没有人死亡的地方。转背的路只会伸延穿过有死亡而没有诞生的地方。
这人的面孔僵死了,他的全部内心生活和动物表情,为了向外传达,都藏在长着毛发的头颅里,在胸膛里,在四肢里。这深藏的生命所有外出的冲动,都在自己的面孔之前退缩,而他的呼吸、嗅觉、视觉、听觉、语言能力,以及作为一个人的光华,都凭着他的胸口、肩头、头发、肋骨、臂膀、腿和脚而发挥功能并且表达自己。
残毁的面孔,罩住的面孔,关闭的面孔,并没有妨害这个人的完整,他并不欠缺什么。没有眼睛还可以看和哭泣。没有鼻子还可嗅和呼吸。没有耳朵还可以听。没有嘴巴还可以讲话和笑。没有额头还可以思想和作心算。没有下巴还可以期望和存活。耶稣见过因残疾而失去机能的人,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我认识这个失去器官的残废人,没有眼睛也能看见,没有耳朵也能听。
那房子没有人住了……
“那房子没有人住了,”你告诉我。所有的人都走了。客厅、卧室、院子,都是空的。因为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没有人留下。
我对你说:人离开的时候还会留下。只要有一个人经过,那地点就不荒凉。荒凉的是人的孤独,是从来没有人经过的地方。新房子的死气比旧房子更沉,因为它的墙里只有石头或者钢铁,没有人。一所房子存在于世,并非由建成的时候开始,是从有人入住的时候开始。一所房子,像坟墓一样,需要靠人生存。这就是一所房子为什么跟一座坟墓那么相似的原故。房子从活人那里得到营养,坟墓从死人那里得到营养。因此前者站着而后者躺着。
在现实里,所有的人都已经离开那房子,然而事实上所有的人都还留在那里。留下的不仅有他们的记忆,还有他们本身。而且,他们不仅仅留在房子里,他们的生活还在房子周围延续。活动和行为,出门乘坐火车或者飞机或者骑马,用脚走路或者爬行。在房子里延续的是器官,是推进和循环的原动力。已经离开的是脚步、亲吻、宽恕和罪行。仍然留在房子里的,是脚、嘴唇、眼睛和心。否定与肯定、善与恶,都消散了,仍然留在房子里的,是行为的主体。
我想讲一讲希望
我感到这种痛苦,不因为我是塞萨·瓦叶霍。我痛苦也不因为我是艺术家、是人,或者仅仅是个活物。我痛苦不因为我是天主教徒、回教徒或者无神论者。今天,我只是单纯地痛苦。如果我的名字不叫塞萨·瓦叶霍,我也同样会痛苦。如果我不是天主教徒、无神论者或回教徒,也同样会痛苦。今天,那痛苦在更低处。今天,我只是单纯地痛苦。
我的痛苦不能解说。我的痛苦太深,从来没有原因也不缺乏原因。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呢?能够重要到停止成为原因的东西在哪里?没有原因;没有原因就可以停止成为原因。这痛苦为什么产生?为它自己?我的痛苦从北风和南风里来,好比某些珍禽在风里产下的中性鸟蛋。假如我的新娘死去,那痛苦不会改变。假如他们割断我的脖子,那痛苦也不会改变。今天,我的痛苦在更高处。今天,我只是单纯地痛苦。
我观察饥饿者的痛苦,我看见他的饥饿比我的痛苦走得更远,如果我绝食而死,坟头还会长出一茎青草。恋爱中的人也一样!他的血比我更浓烈,我的血没有源头,没有人喝!
我一直相信,宇宙万物都是父亲或儿子,那无可避免。然而我今天的痛苦既非父亦非子。它没有后背,天色暗不下来,而它的前胸太宽,天色也亮不起来,把它放进黑暗的房间,它不会发光,放进明亮的房间又不会投射影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今天都使我痛苦。今天,我只是单纯地痛苦。
你们是死人
你们是死人。
变成死人的方式多么奇怪。有人要说你们没有死。然而,事实上,你们是死人,死人。
你们在那薄膜后面的虚无中飘浮,薄膜摆荡于天顶与天底之间,来往于曙色与暮色之间,在并不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伤口前面的共鸣箱里振动。我来告诉你们,生命在镜子里面,而你们就是最原本的,是死人。
而水波漾过来,而水波漾过去,没有阻力,就变成死水。水惟有在撞到对立的岸而破碎的时候会叠起再叠起,于是你们改变了形貌并且怀着信念死去,因为觉悟到第六根弦已经不属于你们。
你们是死人,从来没有活过。有人要说,你们生存在别的时间而不在今天。然而,事实上,你们是从未存在过的生命的尸体。那是从未活过就永远死掉的悲惨命运。是还没有绿就枯萎的叶子。孤儿的孤儿。不过,那些死人并不是、不可能是未曾活过的生命的尸体。他们永远因生活而死。
你们是死人。
把离开你的人跟你……
把离开你的人跟你连结起来的,是回归的共同本能,那是你最大的悲哀。
把留在你身边的人跟你隔开的,是分离的共同服从性,那是你最小的欢乐。
用这种方式,我说明自己,说明集体的个人性,说明个人的集体性,以及那些在两者之间向着边界的声音前进而倒下,或者在世界边沿原地踏步的人。
在强盗和受害人之间有某种中性的、严格中性的东西。它同样可以说明外科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双方都罩在恐怖的、浮凸的、类太阳的半个月亮下面。因为被偷走的物件也有它自己无关紧要的重量,而被切除的器官也有它自己悲哀的脂肪。
在悲惨的生存里找不到快乐的人,在丑恶的生存里找不到美丽的人,世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使人沮丧。
离开!留下来!分别!这几个词语概括了整个社会机制。
总而言之,除了死……
总而言之,除了死,我没有别的方法表明我的生命了。
而且,到了最后,在分段的大自然和麻雀群的终点,我与自己的影子一起入睡,手拉着手。
而且,从尊贵的角色和另一种哀吟退下来,我就歇着思考时间坚决的步伐。
那么,如果空气这么稀薄,为什么要绳子呢?如果钢铁能够独立存在,为什么要锁链呢?
塞萨·瓦叶霍,你藉以爱的口音,你用以写作的语言,你赖以聆听的轻风,只凭你的喉管认识你。
塞萨·瓦叶霍,怀着你含糊的尊严,带着那蛇形装饰和六角形回声的新房,下跪吧!
回归具体的蜂巢去找寻美吧;给开花的水松木添加芳香,封起通向愤怒猿人的两个岩洞吧;最后,修补你那使人厌烦的驯鹿,为自己难过吧。
因为没有别的东西比被动语态的憎恨更浓烈,没有比爱更贫乏的乳房!
因为我已经不能走路了,除非有两座竖琴!
因为你已经不认得我了,除非我机械地坚持跟随你!
因为我如今不发送蛆虫了,只发送短音!
因为我已经把你牵缠到瘦掉一半了!
因为我现在带着一些羞怯的蔬菜,也带着勇敢的蔬菜!
既然晚上在我的支气管里爆裂的慈爱是一些神秘的教区长老白天穿戴的衣饰,而且,假使我在黎明时分是苍白的,那是由于我的工作;假使我在入夜时分是红色的,那是由于我的工匠。这同样可以说明我这种疲倦和这些废品,我的名人叔叔伯伯。最后,这也说明了我用来向人类的幸福祝酒的一滴泪!
塞萨·瓦叶霍,似乎
难以想念你的亲戚
知道我被人押着上路,
知道你自由自在安息,
却来得这么迟!
这是什么荣华富贵的狗屁运气!
塞萨·瓦叶霍,我恨你,以温柔的心情!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