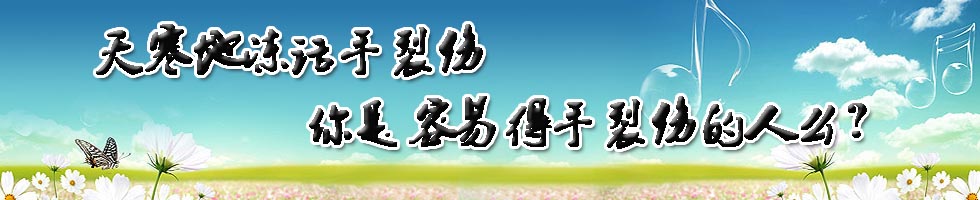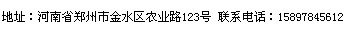转载名家往事胡海波原草青青,我的大
胡海波教授简介
胡海波,年生,吉林扶余人,哲学博士,师从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先生。现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东北师范大学重点建设学科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负责人,东北师范大学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价值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吉林省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周易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逻辑、人与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与精神家园等领域的研究。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实现中国梦研究”。
1大沁他拉草原年的春天与每年的春天是一样的。风以整体的规模席卷着草原上的一切,大地开始翻浆,枯草渐渐地由黄转绿,这是我第一次在这片草原上感受着春天的气象、风沙、泥泞,还有生机和希望。
畜牧排的全体知青,清一色的高腰胶皮大靴子,特别显眼,还带有几分威武。泥泞是路,全排所有的地方到处都是人和畜生踩过的泥泞。尽管这样,排里的人畜还是比冬天热闹与兴旺。温暖的阳光给这里的每个生命带来了新的活力,我和战友们开始谋划整修圈舍,筹集草饲。
正在我为春天而忙碌的时候,连部的文书突然到畜牧排来找我,说指导员叫我去连部。我放下手里的活,用水管子冲刷掉大靴子上的污泥,和文书奔连部走去,一里多路很快就到了。我看着指导员若有所思的表情,不知道他要和我说什么。他像往常一样,和我唠叨几句连里的事情,然后平静地和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上大学,一会儿就去校部报到。我听完指导员平静而肯定的这两句话,顿时惊呆了!上大学?没听错吧?这是真的吗?
指导员看着我吃惊的表情说:“你不是想上大学吗?这回先让你上一回战校的五七大学,时间是半年。”我明白了,是让我去上五七大学。能去学习令我非常激动,管他呢,五七大学也是大学!我都不知道是怎样感谢指导员,以及如何向老首长道别走出连部的。很快我就到了校部政治处宣传科,领取了入学通知书和入学须知。战校组织机构健全,按县团级建制,职能部门一样也不少,其中政治处尤其正规系统。五七大学就是政治处刚刚创办的培养知青骨干的培训性机构。首次开办的是理论班,目的是为各个连队和机构培养理论骨干,也为政治处和相关处室培养人才,具体业务由宣传科负责。
我回到畜牧排,告诉战友们这半年我要去五七大学上学了。大家自然是羡慕与祝贺我,帮我收拾行李,一挂马车把我送到五七大学的驻地。五医院的里院,医院住院部的病房,与医院门诊相对隔离,是一个由三栋土房和一面围墙构成的小四合院。院子清爽洁净朴素,四周由笔直笔直的大青杨树包围着,院子旁边有一块空地,可以露天上课,也可以打排球或羽毛球。
我走进五七大学的办公室,见到一位白发清癯,中等身材的长者,他旁边的老师介绍说这位是王博校长,说话的老师姓林,南方口音与模样,个子不高,穿一双圆口单步鞋,带花框眼镜,文气儒雅。如果他不介绍,我们真的猜不出谁是校长。办完了报到手续,就算入学了。小院子里陆续来了报到的新同学,每个人都是由马车或拖拉机送来的,一共21名学生,男女生差不多均等。学生住一栋房子,房间大小不一,住的人数也不等,与学生相对的那栋房子是办公室和教室。里边那栋房子是食堂和餐厅,倒也齐全。
用现在的话说,这所大学最豪华的不是这里的院子和学生,而是校长和教师。用民国教育家梅贻琦先生的话说:“大学者,大师之谓也。”何谓大师?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不确定的,故而大师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如果可以这样理解,按照我后来体验到的教育与影响来说,战校五七大学有着自己的大师,而且相对于我们这些知青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而言是当之无愧的。被我称之为大师的教员是当时战校的五大才子:王博、李伟实、杨宗翰、米志国、曹志刚,这几位先生都是国内六十年代初期毕业于著名大学的高才生,到战校前大都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专业的研究工作,那时有幸结识这些先生,对我的影响极大,意义无限!
王博校长是书法家,字迹融会百家而自成体系,刚劲隐于柔缓圆润,给人以滋养身心、如沐春风之美感。他每天像上班族一样按时上下班,亲自打扫卫生、打水,处理完校务就开始写字。他每天有写不完的毛笔大字,我们没事儿时看他写字,听他边写边聊书法的识见体验,叫好他的神来之笔,慢慢地成为我们师生之间的审美享受。当时不觉,好多年后才意识到,没有给我们正事上过课的王博校长,其实是以最多的学时让我们领略与见识了当时在战校最好的书法美学,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我在书写中所追求的工整柔顺,就是受此熏染而来的,就连思维、态度,以及处世方式都潜移默化地有所改变。当时我们年轻,一度以为王博校长不像校长,也没给我们上过课,对我们的教育与影响不是很大,现在看来这个评价有失真实,这种润泽的教化是形神一体深沉绵长。在我的心里,这位校长身份的书法教育家,教人不讲课,一切尽在挥毫运笔之中。
大学总是要上课的,五七大学也不能例外。只有一个理论班的五七大学,二十一个学生,六位老师,师生戏称“二十七个半”。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杨宗翰老师自己占一个半,他讲的马恩列斯经典,米治国老师的文史研究方法,李伟实老师的理论教育与宣传,曹志刚老师的文论写作,这些课程构成了五七大学理论班的课程体系。虽然课程不多,但如此的教师阵容与教育思想却给我们这些知青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改变了我们的精神世界,甚至改变了我和其他几个学员的命运。
给我带来最大的人生命运影响与思想理论震撼的是杨宗翰老师。他的经典课让我初识马恩列斯的思想理论及其别样的理解。也让我走近了杨老师的精神世界。杨老师在来五七大学之前是战校中学的历史与政治教师,他的家住在我舅舅家隔壁,我先前就见过他,只是他清高寡言于世俗生活及其交往,没有机会和他说过话。他清癯高挑,高度近视,夏天常常一身蓝白裤褂,圆口布鞋,打鱼打草时总是带着书和辞典,教儿女识字用的是他的老本行看家本领,让刚上小学的孩子逐字逐句认读与抄写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他自己的大块儿时间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学外语,撰写《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的索引。他的阅读专业而广泛,俄语、日语、英语都达到专业阅读与翻译的水准,思想理论经典的熟读与研究水平之精深,这一切都让我们这些知青投地的崇拜。
杨老师给我们上课了。搬来一大摞十几本《马恩全集》《列宁全集》的书,上课时不时地打开其中的某本书快速地找到他所要的内容。这个功夫征服了我们,尽管我们还有些不知所云。杨老师讲马列经典不拘泥于篇章概念,长于抓住问题,提出自己的问题与观点看法,然后引经据典地讲解。我当时如在云里雾里,似懂非懂,倒也觉得有幸师从高人长了见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杨老师对当时党的基本路线的评价和批判。那时面对一统天下的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在我所接触到的日常生活世界里,有谁能思考其正确与否,甚至提出不同的看法,又有谁敢说个不字儿呢!当我第一次听到杨老师评价与批判党的基本路线时,心里紧张极了,也感觉到同学们的呼吸与面色有了异样,担心杨老师会有不测与危险。杨老师好像并不在乎我们的神情,严肃地讲述着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马恩列并不主张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继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而应该是主要搞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他接着就是翻书给我们讲马恩列的经典根据,进而批评当时中国的理论家教条慵懒,自己不研究,照搬照抄苏联的理论和经验。在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杨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观点与道理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正常啊,可是那时我乍听起来既是振聋发聩,又有些觉得费解,但最后还是被杨老师说服了、相信了。不仅在于他讲的理,还在于他在我的心中是怎样的人。我是信奉因人服理的,这是我学习的逻辑。一如我在后来博士答辩时对答辩委员会的老师们说:之于高老师培养与教诲的恩德,我想用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反题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即“吾爱真理,更爱吾师”。因为在中华文化的德性中,真理是相对变易的,吾师是绝对永恒的。
杨老师不仅博学,而且多才。语言文字的造诣和感觉出神入化,表达精准真实,言忌虚妄浮华,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猜想可能与他出身东北师大历史系有关。接触多了,同学们和杨老师有了亲密的感情,他也和我们愈加平和地相处,不管有课没课,一有工夫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交谈、游戏。杨老师擅长写作歌词与谱曲,坦言是母校要求与给予的素养,在我们的要求之下,他创作出五七大学校歌,独立完成了作词、谱曲与教唱。我至今还记得几句歌词:
我们继承抗大的传统,
教育革命再立新功,
牢记党的教导,
肩负着无产阶级的重任,
努力学习,
掌握本领。
……
这首校歌有那个时代的主题与痕迹,但难能可贵的是有着独特的历史感、角色感和责任感。我现在觉得,这三种感觉触及到了教育的本质,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一首经典的大学校歌。
杨老师的多才还在运动上。独处时,他的太极拳如诗如画,会让周围的世界彻底的安静下来。我们远远地望着树林里飘然而动的武者,分享着他的静气。杨老师医院废弃的排球场,画出标准的白线,教会我们打排球。当时在战校盛行篮球,其他球类运动不普遍。杨老师带着我们每天打两场排球,大都安排在上下午的课间,时间长了,我们的球技见长,引得附近连队与机关来比赛,这给冷清的五七大学带来了生气与活力,扩大了影响。这些活动不仅改变了我,也让我见识了我心目中的学人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使我对学问、人格、理论知识与思想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尽管是肤浅的、有限的。杨老师让我看到了过去我不曾涉足的理论天地与思想境界。通过杨老师,我开始朦胧地崇拜思想,这是我在五七大学最为珍贵的收获与改变。
那时年少的我有好多事情是想不通、摆不开的。当我崇拜思想的时候,想不明白文学之于我该怎样安置。这个冲突事出有因,我在五七大学学习的空余时间完成了两个习作,一个是写我当看瓜人之感悟的散文,题为“瓜园熟了的时候”,我描写瓜的生与熟,以此喻人的成长与成人,我强调瓜的生熟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瓜的种子与环境,还有种瓜的人,人亦如此。另一个作品是我写的一首政治诗。我把两篇习作分别给杨老师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李伟实老师,还有他的同学、妻子祝老师,以及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的曹老师,请他们给看看。我的真实意图不仅在于习作的评价,更主要的是想从老师的评价中探寻我之于思想研究与文学创作如何选择。这在当时对于我来说是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问题。
杨老师肯定我的作品有思想品质,在他看来我通过文学创作表达思想,不如系统地学习与研究思想,说我更适合哲学,愿意长期教我。即使是在五七大学毕业以后,几位学文学的老师对我开展了善意的文学批评,主要是说我的注意力过于倾向道理,情感、形象、文字都有些问题,结论是可以继续写下去,但要在文学本身上下功夫。老师们的精神会诊及其结论与建议,把十九岁的我陷入到痛苦的矛盾之中,自幼喜欢却雾里看花的文学与刚刚相识却一见钟情的哲学,我都喜欢,割舍哪个都是痛苦的。那时我要是学过辩证逻辑该有多好啊!天哪,我怎么办?无奈之中我给文学社的姜铁军兄写信商量,数度通信,基本的话题是他问我何以能学习哲学?我和他说“吾马良,吾用多,吾御者善”的条件,其实就是说有杨老师。后来铁军兄见我铁了心啦,最后留下一句话,无论是学哲学还是文学,愿我们就像木匠和瓦匠能成为好朋友一样,要永远是好朋友。铁军兄此话后来真的应验了,我们同在母校学习,他读文学,我读哲学。他一直在搞戏剧创作,我一直从事哲学教育与研究。我们好多年没见了,在彼此的心里,我们是木匠与瓦匠一样的好朋友。
半年后,年的九月,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从五七大学毕业了。老师们留在那里,我们重新回到各自的连队。后来21名同学各有进步,有三位考上大学深造,其中最后考上大学的是我。
2
年的秋天是一个多事之秋。毛主席逝世的悲痛氛围弥漫在战校的整个空间,全校人员胸前佩戴白花,臂戴黑纱,集结在校部附近的空旷草地上,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悼念大会,草地上的秋风卷着我们的悲戚为英魂所破歌。刚刚从五七大学毕业的我,和老兵与知青战友站在草地上肃立默哀,那一刻我年轻的情感世界,经历着不能承受之重的理想主义的焦虑。
化悲痛为力量的信念,把我们从举国哀痛的心绪带回到现实的实际生活中来。在读五七大学期间,我依然当着畜牧排副排长,时常回到排里看看。我从五七大学毕业回到八连,原本以为还会回到畜牧排工作,我还真想念那里的味道和气息。没想到回到连里向连首长报到时,自己的工作岗位有了新的变化,指导员告诉我白城又要来一批新知青,组织上决定把原来的三个班的大田排扩充为六个班的加强排,派我去当排长。听到这个决定,我感觉到了担子的沉重与压力。迎接新战友的首要事情是安排宿舍,秋意渐浓的凉意告诉我,足够的房间与温暖的火炕是最紧要的。于是,我受命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修缮全连的火炕,让新战友感受到火红的砖地滚热的炕之温暖。
大田排的小伙子们是有绅士风度的,承担起给全连维修火炕的任务。这个活有三个主要环节,最基础的是脱大坯,然后是盘炕,最后是抹平烧干。脱大坯是农活四大累之首,用粘土与麦秸和大泥,再用钢叉装入放置在平地上沾了水的坯模子,用手按实四角并使中间饱满,然后蘸水抹平,拔出坯模子,一块标准的大坯就成了。秋高气爽是脱坯的好时节,老天作美我们顺利地脱完所需要的大坯,晾晒干透以至于用。接下来开始的盘炕是个技术活,要用土坯搭成走烟保温的花道,再用坯盖上炕面和泥抹平,烧干就成了地道的火炕。经过天津知青瓦匠老叶的指导和培训,我们全排都学会了盘炕。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各自为战,很快就把两栋房子的火炕搭完了。
我在战校学会好多手艺,饲养、赶马车、开拖拉机、理发、拆洗被褥、做针线活,搭炕,还有盖房子、做饭等等,用到什么学什么。后来上大学时我常在中午休息时给男同学理发,帮同学缝被子,都是那时学会的生活本领。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当了班级的生活委员。
白城的新战友来了。新组建的大田排有六个班,每班12人,清一色的男生,加上我们三个排长排副和一个统计,全排76条好汉住在一栋房子里。每个班一间屋子,正副排长和统计四人住一个房间。标准的南北炕相对,红砖铺地,中间有一个用半个油桶搭起来的取暖火炉,可以在它上面烤馒头片和土豆片,还可以在晚上烘烤湿漉漉的鞋子、鞋垫和袜子。我刚来到八连时的半褥之辱,一直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当下我要实现那时的诺言,绝不让新生蒙受我当时所遭遇的委屈,遂传令禁止挤占新生铺位,不许抢吃新生食物和污损他们的物品,要让新生感受到兄弟般的温暖。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的做法带有书生式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
下乡总是要干活的。随着季节的变化,大田里的玉米成熟了。收割玉米是一年中较为艰苦的劳作,站杆、扒皮、下棒,放倒秸秆,收玉米入场院,拉回秸秆上垛,脱粒、晾晒、交粮,这些活计从十月开始一直要干到隆冬,甚至还要晚些。我作为排长要安排秋收各个环节的人力、物力,保证进度和质量,还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冲锋在前连续作战。
入冬以后,收粮与送粮的忙碌达到了24小时人停车不停的状态,我有时会白班夜班连轴转。那时的我正当青壮,不知疲惫,吃得起辛苦,在草原凛冽的寒风中头戴护住整个头和脖子,只漏双眼的佐罗式毡帽,身着爸爸上大学时穿过的蓝布棉大衣,腰系练武用的黑色板儿带,用几十个别针别住从腋下直至大衣底边儿的开线棉花与布面,形成一道银亮的白链,脚上套着毡袜和45号特大号棉水乌拉,真有点像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这身古怪不堪的塞外行头不仅是我御寒的装束,还在危难关头救了我的性命。那年隆冬时节的一天,我带一个班去白城送粮,回来的路上我们手拄着木锨,站在轰鸣前行的28马力拖拉机上。由于连日的劳累与困倦,我们在没有栏杆的车厢里站着打盹,不知什么时候我竟然睡着了。随着拖拉机加油的耸动,我不知不觉地向后一点一点移动着,移动着,当我移动到小腿紧挨车厢后挡板时,随着拖拉机的又一次抖动,我失去了重心与平衡,重重地大头朝下折了下去,摔在冻得裂口子的板儿油路面上。我不知道昏死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我摔下来之后是否有车辆与行人经过。当我醒过来时,睁不开双眼,站不起来,觉得天旋地转,头疼极了。我的意识渐渐地清醒过来,伸手摸摸自己的脑袋,感觉到佐罗式的毡帽还戴在头上,心里不再那么慌张了,再把手伸到帽子里摸摸疼痛难忍的地方,感觉到整个头的肿大,黏糊糊湿漉漉的,我知道这是流出来的血迹。我想这下子完了,真是大难临头了。来不及再往下深想,我要救自己脱险。躺在路基沟里的我看不到路面,也喊不出声来呼救,几次挣扎都没有爬起来,我最终被迫放弃了站起来的念头,求生的本能驱动着我一点一点地爬上路面。不知用了多少时间,我终于爬到路面上,看到有一辆拖拉机远远地开过来了。车在我身边停下来,车上跳下来的是我的战友,这就是我掉下来的拖拉机。原来我掉下车时谁也没有发现,大家都迷迷糊糊的打瞌睡,到连里才有人发现我不见了,马上驱车沿着原路回来找我,刚好在就要经过那里时我爬上了路面,差一点错过去。那时这条路上人车稀少,天已傍晚,如果我还昏在沟里,后果不堪设想。很快医院,这里有优秀的外科医生,经医生诊断,我的头部有严重外伤与脑震荡,颈部与肩部挫伤,别无大碍,要住院观察治疗。
我的摔伤不幸还伴有无辜批评的降临。指导员听说我摔伤又急又气,以为我们在车上打闹所致,在连队公开场合批评了我,令大家引以为戒,安全生产。连里来看望我的战友和我说了这事儿,令我有些委屈与无奈,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会有如此说法。我对待被人不理解或误解的方式是相信时间会证实真相,当然我也怀疑有谁落井下石,给我抹黑陷害。我单纯的内心第一次感受到人言可畏,意识到我也生活在莫名其妙的是非当中。从那一刻起,在我的眼里战校及其八连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这里真的不是花果山和世外桃源,暗流和是非就在自己身边,只是我未曾这样想过也没有意识到而已。这一事件给我的教训与成长是我不幸受伤的意外收获,由此我开始从单纯书生蜕变成长,慢慢学会直面淋漓的鲜血与惨淡的人生,为迎接不久以后接踵而至的遭遇磨砺些许的心理素质。
医院安下心来养伤。没几天指导员来看我了,他已经知道事情原委,希望我不要介意,尽释前嫌,我怎能和心中一直敬重的首长计较,自然是一如既往地追随老兵。五七大学的杨老师知道我受伤了,带着两个天津梨罐头来看我,让我觉得温暖备至,也令我舅舅和认识杨老师的人刮目相看,吃惊不已。在人们眼里,人们通常认为杨宗翰老师不食人间烟火,与人交老死不相往来,竟然去看海波,还拿着当时知青心目中最为美味儿的罐头,一时在我熟悉的圈子里传为佳话。我的伤势恢复很快,伤口愈合,肿也消了,脑震荡的症状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治疗。12月2日,医院度过了自己20岁的生日。虽然没有生日蛋糕,没有鲜花,但指导员和连长,以及战友们接踵而至的探望,特别是杨老师和舅舅的关心,还有大家带来的大量美食,使我的二十岁生日过得极其快乐、极大富足与终生难忘。
和我同住一个病房的连里机务队队长魏和平兄,他是修拖拉机时被烧伤的,满脸缠着白色的纱布,看上去比我的伤势还重。我们都伤在拖拉机上,正可谓同病相怜,一起度过了雪白血红,意外赴难的难忘岁月。后来魏兄被推荐上大学,就读吉林工业大学拖拉机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们隔墙而居,一直有联系,这是后话。和魏兄一个病房,我养伤期间并不寂寞,他长我几岁像位兄长,给我讲了许多他的经历和往事,让我受益匪浅。
不知不觉间,年就要过完了,我们在病房里迎来了年的元旦,各自的伤病经过一个多月的休养基本痊愈,我们开始商量要出院了。还没等我和医生要求出院,老兵连长和指导员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出院,说有重要任务需要我。我说马上向医生要求出院,坚决完成任务。我赶回连队,精神地站在老兵的面前。连长告诉我新任务不是别的,是组织上批准我和连长还有房副连长等五人,参加战校组织的赴昔阳县大寨和林县红旗渠参观团,三日后报到出发。
年刚刚开始,我就在大难不死之后迎来了即将来临的远行。这是我20岁年华中最远的行程,心中一扫伤痛的阴霾,一天晴朗,一地梦想!这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经历与体验。理解与亲情,信任与远行,对于遭遇危险与伤痛的人是最好的药。
年元旦刚过,大寨之行就要出发了。考察参观团由校部政治处组织,樊维森处长任团长,成员来自全校各连队和机关各部门的领导和骨干,全团一百多人。樊处长任命我担任参观团的联络员,直接听命于团长,负责考察参观团的通讯与联络工作。樊处长是战校青年偶像级的领导,具有超强的领导能力,在行政组织管理与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是省内知青工作的知名人士,后来成为战校的党政最高首长,在战校素以超凡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而著称。
出发的前一天,我来到樊处长的办公室,聆听他给我布置任务。他待我亲切和气,话语平易近人,我依然感到有些紧张和激动,因为我面对的是当时我在战校接触到的最好首长,是上万知青中最具影响力的青年领袖。他给我布置的任务非常明确,跟在他的身边,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这次见面虽然时间不长,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影响,感受到了优秀领导人身上独特的非凡气质与摄人权威。我从心底里佩服他,渴望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与模仿到他的风范。我很庆幸,这次旅行是难得的,追随让自己崇拜的人同行更是幸运的。我对这次旅行以及自己可能的经历充满了期待和希望。
出发那天,我们的第一段行程是赶到白城站,乘火车直达北京。当时火车很拥挤,车厢的过道挤满了人,我们的团队有很多人没有座位,也不知道大家是否都挤上了车。樊处长让我到各个车厢清点人数,然后向他报告。我从卧铺车厢出发,挤进水泄不通的普通车厢,在难以通过的过道里拼力地向前挤过去,一个一个地清点和记录着人数。对于我来说,这是一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任务,可是却进行得极为吃力。这是一次难得的令人兴奋的旅行,然而其拥挤在我的旅行经历中却是终生难忘的。好在我当时只有21岁,硬是凭着青春的力气和工作的热情,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直挤到最后一节车厢,清点完团队全部成员。当我满头大汗挤回到樊处长身边向他报告清点结果时,樊处长说我经受了一次可遇不可求的锻炼和考验。当时我还不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后来在与樊处长的交往中,才慢慢意识到这次平凡而难忘的经历对我的意义。
走出北京站时,我为自己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而激动不已。政治与文化的北京给我太多的印象,可是作为地理与城市的北京于我是完全陌生与新鲜的。在这块神往已久的土地上,我的全部热情与活力被激发出来,真想尽量地多走走、多看看,这是当时最大的愿望。
到驻地安顿好以后,我们很快就赶到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在宽阔的广场上,我久久地凝望和注视着近在眼前的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虽然它们并不像我心中想的那样巍峨高耸,我还是感到真实而亲切的心灵震撼。摄影留念之后,我们依次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踩着施工挖出来的黄色泥土,经过正在开工修建的毛主席纪念堂。
我们在北京停留了两天,然后乘火车赶往郑州,再从那里乘汽车奔赴山西的昔阳参观大寨,再到河南的新乡与林县,参观七里营和红旗渠……
本期编辑:孙然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