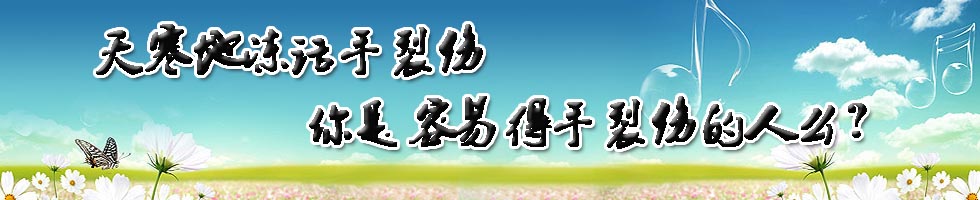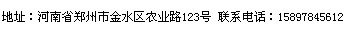经方大家黄仕沛教授临证应用交流实录
黄仕沛教授讲课照片
编者按:
黄仕沛教授为大家作了〈读《伤寒》,用经方,联系临床,还仲景本原〉的专题讲座。黄教授应协会邀请,从广州赶来,从《伤寒论》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到以干姜为例,以仲景释仲景,从仲景书中探索其用药规律,到如何结合临床理解麻杏甘石汤证、白虎汤证、大承气汤证等条文,到伤寒和金匮中的证候群分析(木防己汤证及病案分析),再到蜘蛛散、回魂汤这些行之有效的经验方讲解等等。
会议现场照片
讲课PPT
读《伤寒》、用经方,
联系临床,还仲景本原
作者:黄仕沛
《伤寒论》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我今天的题目是读《伤寒论》,用经方,联系临床,还仲景本原。主题是怎么用经方。什么叫经方,刚才秘书长也说了,汉唐的方都可以叫经方,现在基本上把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里的方子,都叫经方,当然这些含义都是我们的理解。既然研究经方离不开《伤寒论》,那么《伤寒论》是一本是什么样的书,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它,历代的注家有很多说法。近代伤寒学者陈瑞春,他说过一句话,我们研究《伤寒论》走了很多冤枉路,《伤寒论》到现在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了,所谓冤枉路,就是在文字上注来注去,离开了临床。他说我们研究《伤寒论》总是希望把《伤寒论》说得更透彻一点,更明白一点,有时候不免为注而注。我题目的下半截是联系临床,还仲景的本原。仲景原来是什么意思,不是在书房里想出来,所以注来注去就失了注疏的本意。所以陈瑞春说对初学《伤寒论》的同志,不要看张说李说,陈修园的注解是陈修园心中的《伤寒论》,柯韵伯的注解是柯韵伯对《伤寒论》的理解,这都不能代表张仲景的本意。我们研究《伤寒论》的有一句话,一家有一家的伤寒,一家有一家的仲景。《伤寒论》是一本奇书,它历代的注家大概有多家,到近代起码有家。家谁说了算,谁也不能说代表了仲景的本意,所以要还原《伤寒论》,要理解《伤寒论》的原本。
我认为不是所有的诸家都不对,联系临床的就对,离开临床就不对。《伤寒论》是一本很实在的书,现在学院里面把《伤寒论》安排在基础课,我们广中医就属于临床基础,但是有些把它安到理论课,所以很难理清《伤寒论》是一本什么书。如果想治病,离开了《伤寒论》能治好病吗?当然可以,打了折扣而已。所以要提高临床水平和能力,我觉得还是不能离开《伤寒论》,学习《伤寒论》可以提高临床疗效,清代《四库全书书目提要》说了一句话,介绍《伤寒论》的时候,它说仲景书但得其一知半解,便可起死回生。
四库全书书目
我们学中医,都是希望完全理解它,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真的能完全理解它了,历史上就没有三百多家注家了。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很实在,一知半解就可以,读书不一定要把它弄的通透了,一知半解我觉得是《伤寒论》的特点,怎么说都没用,怎么用才实在。用得上,用的对,就可以起死回生。所以《伤寒论》是一本直截了当的临床书,从《伤寒论》的条文来看,都是白描的手法,有什么写什么,所以实际上我认为《伤寒论》是一本临床的记录,张仲景临床上见到怎么样,他就写什么,所以它有一定的规律,也有一定的临床的实践性。
一、以仲景释仲景,
从仲景书中探索其用药规律。
我今天的内容,从六方面讨论。一是以仲景释仲景,就是以仲景的条文解仲景,从仲景书里面探索其用药规律。现在的注家很多,是用自己的理解去注解《伤寒论》,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不一定是张仲景原来的想法,比如第一个注伤寒论的是成无己,他是以《内经》解《伤寒论》,但是张仲景不一定是根据内经来的。大家都知道伤寒论序里有一句话,撰用《素问》《九卷》......,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样写成《伤寒论》。但是从《伤寒论》的内容看,没有引用内经的一句话,没有引用内经的一首方,反而伤寒论里边有很多方子,是当时在民间临床比较流行的,我等一下会介绍。所以要理解张仲景,我觉得不是从内经去理解的,但是从内经理解伤寒论不等于不对,你用内经的道理解《伤寒论》,只能说内经的理论对,不等于张仲景会根据内经去写《伤寒论》,是这个道理。
学伤寒论直接一点,以仲景释仲景,这个是我老师教我的。因为我60年代初上学的时候,当时没有什么教材,全国还没有统一教材。我的伤寒论老师上课的时候,就让大家把《伤寒论》里所有含有甘草、当归、人参的条文找出来,这样来摸索仲景的用药规律。
比如干姜是一味很常用的药,《伤寒论》、《金匮要略》一共用方48次,我们经常看到的方很多都有干姜,比如甘草干姜汤、理中汤、肾着汤、四逆汤、小青龙汤,这些都是有干姜的,我就把所有含干姜的方,都列出来,看这些方是治什么的?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干姜的方有一个共同特点,病症都会有分泌物、排泄物、呕吐物。比如《伤寒论》书上说的,如“吐涎沫”、“遗尿、小便数”、“鼻塞清涕出、“下利”等属清稀的,临床上甚至引伸到疮疹分泌物、白带等是清稀者。分泌物凡是清稀的肯定用干姜,干姜辛温,此功能是他药难以取代的,这是张仲景的经验了,从张仲景的方里就可以摸索,不用看那么多注解的书了。临床上根据规律可以引申到什么呢?除了呕吐物等,有些分泌物,比如疮疡、疮疹里面有分泌物的,白带有分泌物的,如果是清稀的都可以用干姜,鼻塞、流清鼻涕,比如过敏性鼻炎,《金匮要略》是用小青龙汤的,是张仲景的经验,所以也符合《内经》。我刚才说《内经》解伤寒行不行呢?可以。《内经》病机十九条里说了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干姜是散寒的,温里散寒。其实温里也不等于完全是里。所以具体到诸病水液,澄澈清冷,我们都要用温药。用温药具体到是什么药?在《伤寒论》里就是干姜。你用附子行不行?不一定行。不是凡是温药都可以,它有具体的用药,不能太抽象,张仲景的东西不一定是抽象的。
我这里有一个病例,病人不明原因口吐清液一年,病人是四川人,年4月来看病的。病人一年多来每天频频吐唾痰涎,他说是痰,检查胸片、胃镜都正常。一天大概每一两分钟就要吐一次,在我的诊室门口候诊一个多小时,用了一大堆纸巾。这个就要用干姜了,分泌物比较清晰的,他的痰是很清的,水一样。《伤寒论》第三百九十六条,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这个病人就是喜唾,吐一些口水就是唾,很久都不好,一年多了,胸上有寒,这个病人觉得胸部、背部都是冷的,这是寒冷,用理中丸。理中丸如果用汤剂就是理中汤。理中汤的基本方是甘草干姜汤,用干姜最基础的是甘草干姜汤。我刚才说所有用干姜的方都有甘草干姜汤,包括了理中汤、小青龙汤,寒热并用的泻心汤。后来我们就用了理中汤合吴茱萸汤,这个病很快就好了,这是他服药后吐泻物的图片对比。
所以张仲景的书很直观的,张仲景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怎么用。干姜也是好药材,不是把生姜晒干,就叫干姜了。干姜是四川的生姜,是老的生姜,不是厨房里面放干的。那是好药,跟一般的药不一样。药材的质量很重要,医药是不能分家的,我非常同意宋总刚才说的,作为中医,没用好药真的是耍流氓,刚才我们交流的时候,我感觉近年来医药分家是不对的。中医从来就没有医药分家,一分家问题就来了,怎么监控药,甚至是把药当做农产品,农民不管质量,他能生产就行了。所以我非常同意宋总的理念,要把药搞好。
二、结合临床理解条文,毋庸过多暇想。
第二个问题就是结合临床理解《伤寒论》的条文,不用过多遐想。刚才说有些注家,有时候就是遐想,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没责任,跟临床脱离了关系。那我们怎么用经方,就不能用了。刚才说一知半解,不一定要很理解,刚才说的套条文,大病差后先不管它,喜唾就可以用理中汤了,很直观,《伤寒论》的条文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从临床上去理解它。
我举一个例,《伤寒论》的条文大家都很熟。麻杏石甘汤,我们常用的方,也是名方。在《伤寒论》出现了两次,两处的条文基本是一样的,第63条和条。63条说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条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下面都一样的。一个是发汗后,一个是下后,这个前提我们可以暂时不管,后面这几句怎么理解?很多注家都有很多发挥,有些注家觉得这个条文是错的,汗出而喘,汗出能用麻黄吗?为什么汗出张仲景还用麻黄?有汗不是不能用麻黄吗?另外无大热为什么还用石膏啊?很难理解,其实这是一个临床的条文,临床上看到过这些病,我们就知道张仲景的伟大。
前段是不可更行桂枝汤,不可更行桂枝汤是什么意思啊?桂枝汤是解表的方,太阳中风的方,汗出发热恶寒,脉浮缓。但是这个情况下,张仲景就警告我们不可更行桂枝汤,因为不是桂枝汤证,不是表证。但是现在所有的教科书都把麻杏石甘汤当作一首解表清热的方,临床上可以这么用,但也许不是张仲景的原意。汗出而喘,主要是喘,无大热是这个病的伴随症状,喘是怎么回事?喘得厉害就要出汗了。大家可能没有经历过喘,我经历过,有一天晚上我喘得不得了,冒汗,几乎要急死,喘不过气来就出汗冒汗,所以这时不要把它看成是桂枝汤证。刚才说桂枝汤是出汗,无大热的,桂枝汤是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翕翕发热怎么理解?翕上面是联合的合,下面羽毛的羽,就是好像羽毛下面的温度,鸡翅膀下面的温度,这是桂枝汤的发热,不是大热,所以张仲景特别说出来无大热,但是要跟桂枝汤鉴别,不是桂枝汤证。大青龙汤就是大热,大青龙汤全是温药,它是治高热的,无汗出,有汗出大概都是无大热,内经说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很高热的时候一出汗就降温了。所以这个无大热不等于没热,是暂时没有热,你看到的时候没有热,喘得厉害就出汗,出汗热就退了。
历代怎么理解这个方,我举张锡纯的理解,为什么要举张锡纯?张锡纯是近代很有影响的中医,我非常崇拜他,他的书我经常读。但是我觉得他错误理解条文会误导我们,所以现在用麻杏石甘汤,都不是根据张仲景的剂量去用,是根据张锡纯的剂量去用。张锡纯说,我用这个方的时候,石膏的分量恒为麻黄的十倍。就是麻黄用一钱,石膏就要用一两。如果遇有不出汗的,为什么不出汗?他感觉麻黄用的太少了,一钱麻黄出不了汗。这时他说可服阿司匹林一瓦许,以助其汗,若如热重者,石膏又可多用。
张锡纯是近代的大家,他说的话很有影响力。为什么我说他错了,张仲景说不可更行桂枝汤,不是表证,不用发汗。这时麻黄是不是用在表证的,不要一见用麻黄就一定是解表,一见用桂枝就一定是解表。张仲景不是这样的。那么他还用,说明张锡纯用麻杏石甘汤是用在表证,还是有发热的,觉得发汗不够,所以就加阿司匹林。大家知道阿司匹林发汗的力量比麻黄要强得多。张仲景说已经出汗了,你还要发汗?张仲景说不是表证你还要解表?就说明他理解错了。这个证不是表证,另外石膏大量就可以监制麻黄发汗了吗?不是的,这个影响很大。他说十分之一,所以现在教科书都是这样的,很多医生都是这样,用麻杏石甘汤的时候,麻黄只是一钱。但是为什么还要用阿司匹林,他就不理解了。我们知道凡是汗出的,肯定无大热,是张仲景根据临床上看到病人记录的。病人来的时候是喘、出汗、没有高热,就不是我们怎么去想它。
汗出不等于不用麻黄,因为不能光看药物本身,还要看用药的剂量。麻杏石甘汤,用麻黄是张仲景用麻黄的方中最重的,我这样说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因为大家可能没有细心比较过,没有从张仲景的规律去发现问题。表面上用麻黄最重的一首方是什么?大青龙汤是六两麻黄,麻黄汤是三两麻黄,小青龙汤是三两麻黄。大青龙汤、麻黄汤、小青龙汤,都是用麻黄的代表方,大青龙汤,每次是二两;麻黄汤,小青龙汤每次是一两,都是分三次服。大青龙汤方后云:一服汗者,停后服。麻黄汤方后云:余如桂枝汤法将息。桂枝汤是: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说明大青龙汤、麻黄汤是为了发汗。但是麻杏石甘汤没有说得汗止后服。麻杏石甘汤是用四两麻黄,就比麻黄汤要重了,就不是张锡纯说的一钱麻黄这么少了,四两麻黄,半斤石膏,半斤石膏就是八两,是二分之一的比例,不是张锡纯说的十分之一,跟张仲景是不一样的。你说他是经验用药可以,但不是张仲景的用药。麻杏石甘汤,四两麻黄,怎么服呢,分两次服,每次二两,就跟大青龙汤的用量等同了。但是大青龙汤有可能是吃二两就够了,分三次,好了就不吃了。但是麻杏石甘汤是分两次服,张仲景没说吃了第一次好了就不用吃第二次,所以第二次都要吃完,就是一天四两要吃进去,大青龙汤六两不一定全吃进去,麻黄汤三两不一定全吃进去,是吧?所以我说麻杏石甘汤是张仲景用麻黄最重的一首方。
张仲景的书在宋代被整理过,麻杏石甘汤后面有几句话,温服一升,本云黄耳杯,这是什么意思?宋代的名医整理《伤寒论》时看到一个版本,喝黄耳杯这么大一碗的麻杏石甘汤,就不是分两次了,有可能张仲景原来是四两一次服的。我去年到南京,参观了两个博物馆,南京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实物叫耳杯,这是汉代的耳杯,长20公分,高15公分,宽15公分,这样的一碗药是很大。另一个是孙权博物馆,也有一个漆耳杯,大小差不多。黄耳杯是汉代的一种容器,漆耳杯是漆的,估计耳杯容量都是这么大。
上图为“耳杯”
-11-9于南京的孙权纪念馆拍摄
图片源于南京博物馆的官方网站
伤寒论原来有可能是一次就把麻杏石甘汤吃完了,黄耳杯,一大碗。为什么要大量用麻黄呢?如果是一般的喘,张仲景用麻黄不会重的,麻黄的功效其实很多,现在我们会用的都是平喘,对吧?不会用它来发汗了,因为大家都怕麻黄,更不会用它做其他了,包括张锡纯都把它当做平喘药。小青龙汤是平喘的名方,也是三两麻黄,分三次服,就是每次服一两。一两大概是现在的十五克,不算很重。但是麻杏石甘汤是四两一次服,差不多就是现在的六十克了,这么大量的用麻黄,肯定不是为了解表,是为了平喘。喘是一个表面现象,为什么会喘呢?我有一个同道,他在医院的重症室,他跟我说他经常看到麻杏石甘汤的病例,二型呼衰。呼吸衰竭时这种喘,不是小青龙汤能解决的,在张仲景的时代,一定要用大量的麻黄兴奋呼吸中枢。我们现代有很多兴奋呼吸中枢的药,不一定要用麻黄,但张仲景非常聪明,起死回生,所以他要用大量的麻黄,兴奋呼吸中枢。呼衰的病人,一般不会很高热,喘的厉害都出汗了。小青龙汤的喘三两麻黄就可以了,一两一次。但这个四两一次,是仲景的原意,有可能当时张仲景碰到了呼衰的病人。
第二个问题就是白虎汤,我刚才说麻杏石甘汤是汗跟热的关系,出汗就没大热。桂枝汤也是出汗,所以没大热。大青龙汤、麻黄汤没汗,所以它是高热。临床医生都看到,高热的病人大都是没汗的。桂枝汤其实是一种特殊体质的病例,因为又发热又出汗很少的,大都是发热的时候就没汗,所以在表证里麻黄汤、大青龙汤常用,桂枝汤就少用。
我一讲白虎汤大家都有一个反应就是四大,学中医的都知道四大,其实是教科书误导了我们。白虎汤从来不会出现四大,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其实这不是张仲景的原来的白虎汤证。我们看张仲景的原文,没有说这四大证,白虎汤的条文就三条。
条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
条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于转侧,口不仁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
条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
条脉是浮滑的,不是洪大。洪大是虚脉,浮滑是实证、实脉,白虎汤是实证,不会出现洪大的,虚证的时候就会了,为什么说它是虚啊?来盛去衰,来盛就是好像洪水一样来势汹汹,一退就退掉了,这就叫洪。白虎加人参汤证会出现脉洪大,你看16条,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白虎加人参汤是什么情况?会出现脉洪大呢?是一个重证。其实是休克的前期,出现脉洪大。白虎汤证是脉浮滑,是实证。
白虎汤证不会大渴,口渴可以,大渴是白虎加人参汤。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一升水是两百毫升,数升就是大几瓶,喝水厉害是大渴,一般的口干不算大渴,所以白虎汤的四大证是不成立的,大部分是白虎加人参汤的证。如果出现四大,用白虎汤有效吗?肯定没效。没了人参就不是那个意思了。用了人参,白虎加人参汤是休克的前期,津液大量的损耗,所以出现口渴,大喝欲饮,有没有热呢?有可能不会大热,白虎汤没有说高热,白虎加人参汤条说,无大热,为什么无大热?刚才我说了出了汗就无大热,无大热不等于没有热,这个病理的热跟我们体温的热是两个意思,他有热但是体温没有升高,患者是暂时没有热,因为他出汗了,我当医生当了这么多年,很少见到不等于没有,很少见到大汗又高热的。所以我们理解伤寒论一定要根据临床,张仲景是紧贴临床的,他每一句话都不是想出来的,而是见到什么就写什么。
我再举大承气汤证,经常用的,大承气汤有阳明三急下,考试肯定要考的,但是到临床怎么理解就难了。比如条,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溏,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这是阳明三急下的其中一条,为什么要急下?什么叫目中不了了?
目中不了了实图
第条我们对比一下,条是伤寒,若吐若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者,大承气汤主之。表面上看来两个条文,条好像很重,不大便五六日,条是大便溏,另外独语如见鬼状,循衣摸床,很重了,神智有点问题了。但是条说了无表里证,没有表证也没有里证,表面上身微热,不是很高热。为什么这样轻的病要急下,怎么理解目中不了了?古人说的目不了了就是看不清楚、模模糊糊,跟条的直视不一样,直视是眼睛发直,不会转动,很重的样子。但是目中不了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是球结膜水肿,现在医学很重视一点点的症状,都是脑病,比如脑出血,脑炎等等,所以张仲景很聪明,这个时候要大量脱水,快点脱水,所以他写急下之,不是没有大便就通大便,即使是大便溏,也要脱水,古代脱水最快最直接就是泻下,急下之。。见到脑病,目中不了了的时候,如果是中医,一定要泄,快点脱水。
这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的熊医生发给我的,他在重症室里用中药,当然也用西药,他在重症室经常看到张仲景条文的症状出现,这个病人就很明显,65岁,急性心梗,做了支架,后来就心衰,有发高烧、恶心、呕吐,心梗、心衰都改善了,但是高热不退,一直波动在38度到39度之间,身热无汗,凡是高热都是无汗,没有咳嗽没有痰,没有腹胀,盐水灌肠就排出一点点稀水,没有粪便,小便淡黄,舌头特别红干,脉弦数,患者特别想喝水,大渴饮饮,每次物理降温的时候,都想咬掉冰袋里面的冰水,很口干口渴,另外神志不清,眼神发直,呼之片刻才能答应,熊医生就问我,很像目中不了了,他想用大承气汤,他说没有大便,排不出大便,我说是大承气汤,不是目中不了了。那个时候很危险,他说现在用消炎药,等级已经用到最高了,病人夜间烦躁,大呼小叫,吵得病房里其他病人彻夜不宁,请黄老把关。我说用大承气吧,第二天给病人做了腹部CT,发现结肠里果然很多大便,昨天灌肠为什么没有大便,护士灌的不够深,所以排不出大便,后来就用大承气汤灌肠,口服大承气汤,一剂药就退热了,退热没有积屎了,眼神正常了。从临床上就可以鉴别到什么是目中不了了,什么是积屎,所以要多在临床多观察,就能体会张仲景的用意,这个效果我觉得很好,一般的中医都很少有机会看到这么多重病,他是看到一个就用《伤寒论》的条文来对照,他准备出一本书,写《伤寒论》跟重症的一些关系。
三、《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证侯群
第三个问题是《伤寒论》的症候群,症候群是西医的名词,其实中医早就有了,古人观察病人时已经摸索到一些规律,发现这些都是固定的一系列的症状,张仲景更聪明的是一系列的症状他有相对应的方子去治疗,我们现在医学的症候群没有对症的药。凡是治不好的病,或者某某综合症都是治不好的,说不出病名的。但张仲景就有对应的方子,我举几个例子。经常看到狐惑病,狐惑病就是眼睛、粘膜结膜咽部口腔的溃疡,狐惑病是一八七几年才发现的,西医叫白塞氏病,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已经有狐惑病,其实是一个症候群,有这个症状就是狐惑病,所以要重视《伤寒论》、《金匮要略》里面的症候群。《金匮要略》用甘草泻心汤治疗狐惑病,甘草泻心汤在《伤寒论》里是治脾的,《金匮要略》用来治狐惑病,狐惑病跟脾一点关系都没有,临床上用甘草泻心汤治口腔溃疡,白塞病都很好,这说明张仲景是经过临床的。
木防己汤,在《金匮要略》的痰饮篇,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实是一堆的症候群,比如肺心病,支饮就是很多痰,痰太多了又喘,其人喘满,心下痞坚,痞就是按下去不硬的叫痞,按下去硬叫坚,有东西在里面叫坚,痞是病人自己的感觉,坚是医生摸到的,有可能是肝肿大,肺心病的病人都是肝肿大了,面色黧黑是缺氧,肺心病的病人都表现在条文里面。
很多中医教科书或者注家怎么注解呢?比如刚才说的目中不了了是肾水不足,不能上注于目,为什么要用大承气汤呢?急下存阴,把损耗的阴保留了,不能让邪热再伤阴了。但是好像不满足我们,目中不了了还是解释不了,我刚才的解释有可能是张仲景原来看到的病人。如果用中医原来的思维去理解它,喘是什么?有可能是肾虚的喘,面色黧黑,肾的颜色就是黑的,肾不纳气所以就喘了。如果这样理解,能不能还原张仲景的方?张仲景用木防己汤。木防己汤是木防己、桂枝、人参,石膏。问题来了,这四种药能补肾吗?不能,如果用传统的中医的思维不能理解。有些注家说面色黧黑是有淤血,木防己汤能活血化瘀,不对吧?桂枝可以活血化瘀,但不是整个方的意思。
为什么要用石膏?木防己汤用石膏就像我刚才说的麻杏石甘汤,用麻黄用重的一首方就是麻杏石甘汤,用石膏最重的一首方就是木防己汤,不是白虎汤。麻杏石甘汤用石膏半斤,大青龙汤用石膏鸡蛋一枚,白虎汤用石膏一斤。汉代的一两大概是现在的十三克多,或者是十五点多,有两种说法。木防己汤是用石膏十二枚,如鸡子大,汉代的鸡蛋比现在的鸡蛋小一点,有出土的汉代的鸡蛋的尺寸。我一个学生量过,汉代出土的鸡蛋这么大的一个石膏,一个鸡蛋大概50克到60克,12枚的石膏大概多克,白虎汤一斤石膏折算后相当于现在的半斤,克的石膏,木防己汤是用大概克的石膏,是所有张仲景的方里面用石膏最重的一首方。但是为什么心衰的病人用这么多的石膏呢?说不清。所以我说一知半解就可以了。
出土的汉代鸡蛋
近代一位经方大家,现在《伤寒论》的教科书都是他写的,刘渡舟老先生,他有一个医案是说木防己汤的。他说学习痰饮篇的时候,痰饮篇的第一首方就是木防己汤,其他的都滚瓜烂熟了,但是学到木防己汤的时候,就不理解了。这个方为什么要用石膏?说不清。后来他碰到一个病人,囊肿,心促,咳嗽,喘烈,看了很多大夫,都没效果,就找到了刘渡舟老先生,刘渡舟老先生开了苓桂术甘汤,治痰饮的一首方。他说这个方用得非常多,很拿手的。结果用了之后,他的病情不但不见好,还变得更加严重,喘得更厉害,为什么?方不对证,方对证就好了。痰饮病,笼统的用痰饮方可以吗?不行的,所以张仲景的核心是方证对应,有是证用是方,就好像开门锁是一把钥匙,是你的钥匙才能开这个门。所以第二天病人又来了,喘的厉害,晚上不能躺床上,这就是痰饮篇说的,咳逆倚息不得卧,后来又开了一个方,大概是化痰利气舒肺降气,这些抽象的能治好吗?我看刘老先生到这个时候,他想不出用什么方了。所以第三次复诊的时候,这个病人又来了,对他有点意见了,我看了三次都看不好,当然这个病不是轻的,看了很多医生都不好,看到刘老先生是名医,他说三次都不好,有点责怪刘老。后来刘老一想,这个是木防己汤证,面色黧黑,心下痞坚,喘满,隔间支饮。显然是木防己汤证就不能用苓桂术甘汤了,但是刘老想自己没有用过木防己汤,也不理解木防己汤,怎么办?他就硬着头皮开了木防己汤,结果就病人一吃了木防己汤,第二天就好了。
所以张仲景的东西,我刚才说的不是假话,一知半解就可以起死回生。临床上有很多木防己汤病例,这是一个误诊为肺癌的病人,其实是放线菌感染,但是他出现的就是气喘,不能平卧,脸色黧黑,后来我用了木防己汤就好了,这个病人本来在梅州治了三个多月,快要以为他是肿瘤,医院,医院就诊断排除了肺癌,但是症状没有改变,没有好转。后来就请我去,我说木防己汤,很简单,就是防己、桂枝、人参、石膏,我用石膏克,结果这个病人就好了。
另外有一个病人,也是很典型的木防己汤证。我的一个学生,广西中医药大学呼吸科的主任,他碰到这个病人,动则气喘,动则尤甚,头晕干咳,大便一到两次,口唇发干,大便日解1-2次,易解烂便,眠可。口唇发绀,三凹征,双肺音粗,嘴唇发干,脸色黧黑,后来他叫他学生开了木防己汤。病人病情很重,喘得很厉害,肝也肿大,肝肺综合证,在呼吸科在住院。结果吃了两个月之后气喘就缓解,能走两百米,再能做一些家务,那很好了。
5月26号嘴唇颜色正常了,以为好了,就停药了。后来7月28号,嘴唇又黑了,这个病例很有说服力,一用木防己汤就好,不用木防己汤就差,比原来更差。但这个方怎么理解呢,到现在我都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用石膏。
春节前,我在中医药大学急诊室里看到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心衰、气喘,喘得很厉害,每天要吸很多痰,不能平卧,就像条文的表现,在急诊室里10多天,又出不了院,又没有床位,就只在观察室里观察,每天吸痰,后来叫我去治疗,我就开木防己汤,克石膏,结果12点多吃药,傍晚五点多钟病人就打电话给我,他说10几天没有这么好,没有这么舒服,今天出了一大口的稀痰,就不用吸痰了,看来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这个病历我想起来了为什么要用石膏,日本医生解释石膏有解凝的作用,我的理解它的解凝就是能溶解或者是把凝集的痰释稀,原来要吸痰的现在不用吸了,变稀了,痰变得稀了就容易出了。所以呼吸道就通畅了,心衰就改善了。所以张仲景很聪明,不是现在说石膏是清热的,清阳明热,通过临床有可能会理解木防己汤,如果不理解,就像刘渡舟老先生不理解也照用,照用的时候有效,有效就行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一句流行的话,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行动中加深理解。我们把《伤寒论》当做最高指示的话,是我们的经典,不用想的太多。
四、仲景书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成,
其中不乏行之有效的经验方。
张仲景的书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成。所谓博采众方就是行之有效的经验方他就采过来,比如木防己汤是一个很有效的常用方,从张仲景的书里可以看到方很多是他博采众方来的。比如越婢汤,这说明不是张仲景的方子,越国婢女的一个经验方。有些专方专药,比如蜘蛛散很明显是一些秘方了,或者民间方,甘草粉蜜汤,还魂汤,甘麦大枣汤等等。比如甘麦大枣汤也是很奇怪的方子,大家都知道是治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和悲伤一样想哭,所以现代的人引申这个方可以治焦虑症、抑郁症。但是反过来所有的抑郁症你能用这个方吗?不能。因为有些抑郁症患者,有些焦虑症不一定出现喜悲伤欲哭。但是这个方很简单,甘草、大枣、小麦共三味药,百分之七十的经方都有大枣和甘草。为什么其他的方有大枣甘草不能治喜悲伤欲哭,这个方才能治?加了小麦就能治,有人说这个方治阴虚脾虚、肝虚,或者抑郁症就是肝气不疏,但也没有用一些疏肝的药,这三位药也不疏肝。反过来如果碰到喜悲伤欲哭这个病,你再加其他药效果就下降了,我发现很多人用这个方时觉得张仲景太简单了吧,三味药怎么能治好这个病,又加柴胡又加酸枣仁等,就变得不是这个方了,所以用经方一定要纯。这个方宋代有一个医生叫许叔微,他写了一本书叫《伤寒九十论》,他把九十个病例按《伤寒论》的条文,或者是《金匮要略》的条文对照,这个病应该用什么方,张仲景怎么说的。其中有甘麦大枣汤,他碰到喜悲伤欲哭的病人怎么治都治不好,后来他就用甘麦大枣汤,用了之后他说仲景的方用而后知,你用过就知了,不要想三想四,觉得仲景方太简单不够厉害,你就又加这个又加那个反而没效,这个方我经常用,就是三味药。但是比如小柴胡汤也有大枣、甘草,为什么小柴胡汤不能治?小柴胡汤加小麦行吗?不行,桂枝汤也有大枣,甘草,桂枝汤加小麦行不行?也不行,只能三味药,所以许叔微才说用而后知,原来你不相信的你用过就知道了。所以乱加乱减是不相信张仲景,就像木防己汤你相信就用了。
比如蜘蛛散是个很神奇的方,是一个验方,没人敢用也没机会用,本来是治胡疝的,疝气,当然了有很多经方医生用了。比如经方医生曹颖甫写了一本书叫《经方实验录》,里面有几个疝气的病例,他都是用蜘蛛散治好的。前年经方群南阳的苏医生发了一些文章在群里,我问他,你这么有心把这些文章都收集了,后来他就做了一个U盘给我,里面有很多文章,都是说蜘蛛散的。
其中有一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前贵州省的一个老中医,他碰到一个很严重的疝气病人,痛得要死。旅店服务员叫他试试用蜘蛛烤干了口服,结果这个病人真的用蜘蛛,说一吃就好了。这样引起了老中医的注意,他当然对经典很熟了,这不是张仲景的蜘蛛散嘛,后来他就用蜘蛛散来治疝气,果然效果很好。这个老先生很严谨,他说要治好50个病例,他才发表文章,结果用蜘蛛散治了多例,后来才写了一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个杂志里面发表。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的这篇文章。这说明什么呢?第一,经方的来源有民间的验方,张仲景博采众方,第二,这些方都是经过张仲景临床使用的,反复有效的。后来我又找了一些文章,网上有人说了,蜘蛛散的是土蜘蛛,不是结网的那种蜘蛛,是在地上的蜘蛛。
我看到这些材料之后,刚好我有一个亲戚做了疝气手术,三年后复发了,痛了一个多月,腹股沟凸出来。我刚好看到这些文章,我就叫那位医生拿一点给我,给我亲戚吃,他说蜘蛛怎么吃,就装了胶囊,本来是吃四颗,四粒一次,一天吃三次,他就吃了两粒,一天吃了两次,吃了以后整天都不痛了,我说你不怕那继续吃吧,他吃了三天后到现在都没有再复发,剩下四天的的药我又拿给我学生的岳父,他也疝气发作,吃了又好了,所以说有些方不是说理可以说的清,说什么道理都没有用,反正有效就是了。
张仲景的方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还魂汤,我刚才说了,一知半解就可以起死回生,还魂汤为什么叫还魂汤,起死回生就是还魂了。这个方是在《金匮要略》后面一些复方里面的,其实还魂汤是是麻黄汤,麻黄汤另外一个名叫还魂汤。有一个病人,八十多岁,医院副院长的母亲,跟我很熟,她本来有抑郁症,曾经有自杀的倾向,她有抑郁症要吃药,12月19号晚上,她一次大概吞服了片阿普唑仑,10片思乐思,10片思瑞康,都是安眠药、抗抑郁症的药,那个晚上她八点多回房间睡觉,我记得是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早上我同事就回家看母亲,他父亲说她昨天睡的很好,不要吵醒她,那时候八点多钟,再坐一阵子还不见她醒就进房间看她,口吐白沫,昏迷了,立即打电话,医院,医院打电话给我,刚好我去了珠海,我说礼拜天才回来,你就在ICU里面抢救,医院看她,ICU的医生说看来是醒不了了,这么多天了,现在什么措施都做了,还不醒,有可能植物人了。后来我就说可以给中药给他吃吗?他说你开我就帮你喂。我就开了麻黄汤,就是还魂汤,三十克麻黄,三十克桂枝,十五克的杏仁,三十克的甘草。第二天配到药下午四点多就喂药,喂了五点半就睁眼了,家里人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好像醒了,我说那就再配一剂立即煮,煮了七点多就喂她吃第二次,开始有点汗。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坐起来跟我谈话,正常人一样。这个病人连续出了三天汗,过两天就出院了,到现在抑郁症都没有了,不用吃药了,非常好。后来家里人把他送到老人院,我去老人院看她,问她还想不想死啊?她说不死了,现在活得很开心。
故事还没说完,医院的熊医生,他听我说过这个病例后,他也收了一个病人,开始以为是呼衰。病人也是八十多了,昏迷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平常是有慢阻肺的,治了几天无效。后来家里人发现他房里的安眠药全部没有了,想起来他有可能是吃了安眠药,就立即给一剂麻黄汤,按我这个方。我的病人大概是一个小时就醒了,他这个病人两个小时醒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在国外的杂志里发表,内容是还魂汤能起死回生,所以仲景的东西你相信就行了。
五、要用历史的观点看待仲景的条文。
第五个问题,学习张仲景的东西要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待条文。比如书中有误汗误下误吐,很多这样的条文,其实张仲景的时代很多是用外治法治病的,当时不是用汤药治病。当然有汤药,《内经》有十三方。但是张仲景的时代,内服药不是占主要的,很多用了不适当的手段治病。比如发汗,令我们现在对出汗都非常恐惧,因为张仲景经常说误汗,其实当时发汗的方法不是用麻黄汤、桂枝汤、大青龙汤,是另外一些出汗的方法,比如《伤寒论》说的,烧针,温针,火熏,火灸等方法。
汉代之前中国的医学还是很粗糙的,我说是很野蛮的。张仲景有一个条文说,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就是再这样就会死了。我看华佗传就有一个病例,华佗是名医,但是他不是用汤药的,他是外科医生,病人发高烧,华佗叫人家把病人抬放到一个石槽里,像石棺材一样,冷天一大早晨,把病人衣服脱了,以水渗之,《伤寒论》的五苓散条文里有。以水渗之就是用冷水喷他,让他退热,这是物理退热。华佗下处方喷一百次,冷水泼他一百次,结果几十次之后病人冷的不行,要死了,上手的人说可以了吧?华佗说不行,还要继续。张仲景为什么要提倡汤药,就是跟以前的方法不一样了,以前的方法很多,副作用也很多,有很多弊端。《伤寒论》是一本怎样的书?徐灵胎说《伤寒论》是一本误治之书,其他方法治不好的病,就用汤药来治。其实张仲景讲误治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伤寒论》不是光讲外感病,不能把《伤寒论》看作是治外感病的,其实是通过外感病误治之后出现的变证,变成了其他病,《伤寒论》就针对这些问题来处理的。很多方比如炙甘草汤,治什么病?不是太阳病,也不是阳明病,是伤寒的变证,借变证来说杂病,所以叫《伤寒杂病论》。现在教科书说《伤寒论》是一本讨论研究外感病的专书,我觉得此说并不全面,其实是借外感病来说杂病。
《伤寒论》之前的发汗方法是什么?比如《内经》的"渍形以为汗",不是吃了麻黄汤或者大青龙汤就出汗,是一种外治的方法,渍形就是用蒸泡的方法来发汗,《伤寒论》说的以火劫发之,也是野蛮的方法,《伤寒论》说疮家不可发汗,但是《灵枢痈疽篇》怎么治呢?痈疽篇就是生疮了,坐陵翘草根各一升水,以水一斗六升煮之,取三升,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生疮的时候,病人喝这个汤,厚衣坐于釜上,釜上就是上面一个窝下面煮开水,把病人抬上去,这样发汗,有人反对《内经》这些方法了,所以说疮家不可发汗。不是说疮家不能用麻黄、桂枝,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要用历史的方法去看。这种方法就引起了后续的误解,觉得发汗很可怕了,中医说汗为白血,汗与血异名同类,发汗就是败血,出汗就会亡阳,其实是错的,我没有见过出汗亡阳的,亡阳才会出汗,要死的人就出汗了,这个时候不是用药出汗,是他自己有基础病,亡阳了就出汗了。因果倒置了,出汗没问题的。张仲景反对那些用火逼劫的发汗,野蛮发汗的方法。你看《汉书苏武传》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汉代匈奴的时代,你看多野蛮,苏武到了西域就自杀,引佩刀自刺,旁边的人就怕了,叫医生凿地为坎,挖一个坑,置温火,坑里点火,把苏木抬上去,蹈其背,还要踩他的背,他自杀流血过多跟出汗有什么关系啊?苏武就气绝了,说明火逼劫之这种方法在汉代是非常流行的。但张仲景是提倡用汤剂,反过来看出汗不是什么问题,不适当的出汗当然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伤寒论》条文里面的出汗。最明显的就是奔豚,有一个条文说发汗后就引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发作欲死,是误治引发的,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古代的针不是现代的毫针,古代的针比锥子还要粗,铁杵磨成针嘛,绣花针都很粗的,这样的针烧红了,扎进病人身上,当时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差,古代人一看到血就晕倒。我记得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叫《针刺麻醉》,放电影时经常需要我们派医生去电影院准备抢救观众,针刺麻醉开胸膛的时候,很多观众都晕倒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几十年跟现在都不一样,汉代的时候就更不一样,所以用火针、烧针会很多不良的反应,所以我们要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它。
预知更多内容,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