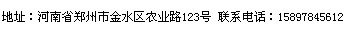年的一场私奔离家出走去敦煌
年春,我16岁,高一在读。
我有一个闺蜜叫顾锋。
顾锋体型强健肤色黝黑,乌亮长发,浓眉下一双迷人的小眼睛。我甚至发现,我后来所爱之男人身上,都有顾锋的影子,尽管她是个女孩。
顾锋人如其名,外表像女汉子,内心却十分纤细。小学四年级,从我认识顾锋的第一天起,我便对她充满好奇。这种好奇的情感一直维持到杳无音讯。她教我看言情小说,她与我描述她的“爱情”,她与我倾诉她的孤苦与她的家庭……她甚至教我骑车做饭与自力更生。顾锋与我同年,四年级我们十岁,可我显得幼稚无知,我惊讶一个人何以如此丰富!我被她深深吸引。从一九八六年初识到一九九三年敦煌之行,我们亲密无间如胶似漆。我用形容恋人的词汇来形容我与顾锋的情谊似有不当,但事实确是如此。我们会像恋人般争吵、冷战、道歉、和好,我常想,也许这才是我爱的启蒙。大部分时候,我们交换心声,追逐流行音乐与各种书籍。我们在雨中一起打球,在居民楼一起恶作剧,一起无端地大笑,也一起因为“寒烟”之流哭泣。一九九三年三月的一个周末,我与顾锋煲着电话粥,天马行空高谈阔论,我清楚记得我们因为一句无聊的玩笑条件反射般笑了半个多小时都停不下来。我们聊古诗,聊塞外,聊梦想,聊风花雪月。最后,顾锋说:我们去远行吧?思考只是一秒钟的事,我们各自找出所有现金,拼拼凑凑两人竟也有一千二百多元。至于行装,也只是一个背包几块饼干一个水壶而已,连换洗衣物都没带。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当时我家门口有开往上海火车站的公交车。下午四点多,我们搭上一辆公交,开始了这段如今称之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出门前的丝丝忐忑,与兴奋与激动相较,连涟漪都算不上。车开到上海火车站停下,接下来去哪?顾锋说,要往西。我虽强势机灵,但在顾锋面前,我更愿意听她指挥。我们在售票厅仔细查找最近一趟开往西部的列车,当天深夜就有一趟去西安。离开车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在火车站广场附近游荡,看到一家理发店,顾锋说:你长发的样子太美,剪了吧。那是我第一次剪成假小子模样。我们还买了几袋面包,打算以此度过火车上的时光。等到了西安,我们才发现面包还可以有别的用途。不记得坐了多久的火车,只记得绿皮车厢硬座挤满了人,汗味、屁味、烟味与食物的味道交相辉映。不记得西安的天,也不记得西安的吃,只记得八元一晚的招待所,还有荒郊野外的兵马俑。在那里,我们用一袋上海面包交换了两袋小陶俑,小贩用新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手上焦黄的面食,问我们这是什么,并主动要求用陶俑换面包。还有大雁塔,上塔门票太贵,我们在底下行过注目礼,便愤愤离去。可以说,西安在我的记忆里,几乎等同于物物交换,别的什么都没留下。在西安逗留了三天,我们意犹未尽,并不打算就此回头,顾锋说,要往西,于是我们又坐上开往兰州的火车。到兰州正好天亮,肚子寡了好几天,打算奢侈地享受一下兰州拉面。可是我并不记得那碗拉面的味道,倒是有一个与拉面相关的人,一直留在记忆中。他是一个军人,右脚有点跛,当时大学毕业没多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他看我们两个外地女孩,好奇地过来询问,请我们吃了拉面,留了联系方式,并约定要写信。后来我们真的通了很长时间书信。高三那一年,有天我放学回家忽然发现他在我家中,他说他来看我。出于对一碗拉面的感激,我带他逛街,请他唱歌,并邀请吴润雨一起款待他。第二天,他说临时接到任务要回去了。后来细细回想,我才意识到,也许我轻轻伤了他。于是,兰州对我而言,成了一个跛脚男青年的缩影。
我们没有在兰州过夜,直接搭乘长途大巴去了敦煌。从兰州到敦煌的一夜,成了我记忆中最漫长最寒冷的夜。三月上海已是暖风习习,可西北仍冰冷刺骨。所有大巴上的乘客都穿着棉袍戴着围巾,我和顾锋只有一件毛衣。我们一夜未眠,互相依偎。看着月亮东升西落,我们以为天就要亮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月亮过后星星又起。于是,我们又蜷缩着看车窗外满天繁星东升西落,如此美景我们全无心体会,只是一味祈祷、等待、煎熬。等到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沙漠,到处荒芜,只有稀稀拉拉枯黄的骆驼刺随随便便耷拉着。顾锋的嘴一直哆嗦着,怎么也合不拢,那一晚,我们冷透了,透透的!顾锋说:鱼儿我冷。我便抱她更紧些。
我不记得敦煌的莫高窟有多迷人,不记得鸣沙山月牙泉有多孤傲,却一辈子忘不了迎接我们的沙尘暴,还有一位美丽的姐姐。一下车,我错乱了!一片昏黄,天地混沌,沙粒无孔不入,从耳朵从嘴巴从袖口从衣领,我们从头到脚像刚从沙堆里爬出来,牙齿缝里都是沙。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六元一晚的招待所,我们赶忙打听这里的天怎么了?招待所的阿姨不慌不忙地告诉我们,沙尘暴,每年都有,赶上了。好吧,我们整个下午都只能呆在招待所,哪都去不了。傍晚我们去招待所旁的小卖店买吃的,碰到一位女大学生,也住在招待所。她在北京上大学,到敦煌看朋友。她问了我们所有她能想到的问题,最后,我们告诉她,我们已经没钱回家了。我和顾锋甚至商量是不是可以一路扒火车回家。美丽姐姐很着急,说扒火车很危险,千万不可以。她说,她也没多少钱,但是他朋友在敦煌做买卖,可以借钱给我们。她跟我们约好第二天带我们去鸣沙山,去他朋友那里借钱。第二天她真的带我们去朋友那里借钱了,她朋友真的借给我们三百元路费,还带我们在鸣沙山玩了半天。我记得那是一个长胡子的叔叔,样子很丑。我们千恩万谢,发誓回去一定还钱。回到家我父亲就去邮局汇款还钱,他说,一定要双倍归还。我还在鸣沙山捡了两块圆润的石头,塞进背包,并一路带回老家。于是,敦煌于我而言,就成了沙尘暴与三百块。既然已经沦落到借钱的地步,我们悻悻,该回家了。从靠近哈密的柳园坐火车,两天三夜,一路坐到上海。期间由于我不够机灵,火车靠站时进了卫生间,又不够仔细,没关严卫生间的窗户,被守在站台边拿着大水管的红袖章大妈用水管狠狠冲了一遍,回到座位硬生生用体温把湿透了的牛仔裤捂干。一路风沙干燥,我的手裂了,顾锋心疼得掉眼泪。当我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母亲的眼光是呆滞的。她没有嚎啕大哭,没有厉声责备,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短头发不好看。于是,我哭了。母亲给我父亲打电话,让他回来。她对我说:你爸爸去北京找你了。后来我才知道,顾锋的父亲甚至去了内蒙古找我们。父亲见到我后也没有呵斥,只是苦笑着说:这袋小泥人和这两块圆石头,挺贵。逃学逃家,我们的“光荣事迹”传遍整个校园。我和顾锋在国旗下高声朗读悔过书,同学们在底下用羡慕也许崇拜的眼神看我们。我和顾锋名声在外,甚至有不认识的同学私语,说我与顾锋私奔去了。在我心里,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从此定义为私奔。可是,我与顾锋的情谊并没有因为这次特殊的旅行而更进一步,相反,我们渐渐生疏。高考过后,顾锋去了厦门,我去了广州。我们仅仅偶有书信,寒暑假也只是偶有往来。大学毕业后,顾锋到杭州工作,我去了英国,从此失去联络,杳无音讯。这么多年过去,顾锋这个名字已经从我所有的通讯方式中消失,了无痕迹。要找到她不难,只需转两三道弯,只是我不曾想要去找她,正如她也从未联系我。我与顾锋的全部情感,永远停留在路上,一路向西的路上,我不愿重逢的生疏污染青春的记忆,就这样杳无音讯吧。
注:顾锋为化名,“私奔”之事却属实。本文写于年,当时我与顾锋已失联多年。年春,同学会的缘故,忽地又有了联络。同年夏,她举家来大理看我,同年秋,我又去厦门看她。那一年,我发现多年不见的我们,竟做着同样的事:她在鼓浪屿开着一家民宿,经营着一间文气息的杂货店;而我在大理开着一家民宿,经营着一间文艺气息的杂货店。两人愉快地交流了民宿平台的客源差异,两地游客的购物喜好以及杂货店的货品货源问题。后来,我们的生活又各自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概我们都属于不甘于重复生活的人,总在身体力行地诠释“无折腾不人生”的含义。
往期文章
你猜,新鲜出炉的摩尔多瓦是什么?
马耳他:看房记
马耳他:穹顶下偶遇一位流浪世界的老人
二十年前和我一起在英国中餐馆打工的那些人
那个在树下弹吉他的男生
更多文章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