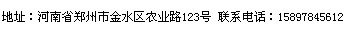岁月有痕林平姐姐二篇
这是作者写于不同时期的关于姐姐的两篇文章。两文时隔十五年,姐姐仍是那个姐姐,作者的思想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中可窥视出社会底层人民的辛劳和不易,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某种特征。
姐姐
我忽然异常想念我五十三岁的姐姐了。
这会儿,姐姐远在东海边的宁波,在姐夫身边。姐夫在宁波打工二十年了,与姐姐总是聚少离多。今年清明节那天,姐姐带着她两岁多的小孙女,跟姐夫一起坐上了开往宁波的汽车,她要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调养身体。待到八九月份,小孙女该上幼儿园了,她将返回豫南小城光山,在家里照顾小孙女。
每次想起姐姐,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为姐姐的身体,为姐姐的操劳,也为姐姐满满的心事。
姐姐在独山章畈的乡下老家生活了大半辈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早年姐姐上初中时,就成了生产队的一个劳动力,跟妈妈一起,撑起了一个家。此后不久,姐姐就辍学了。爸爸和妈妈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姐姐辍学是迟早的事。那时,爸爸常年教书在外,几乎照顾不了家,田地到户后,妈妈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姐姐在读到高一时便不声不响地辍学了。割麦、栽秧、施肥、打场,所有女人干的活,她都要干;犁田、耙田、挑草头、挑粪水,所有男人干的活,她也能干。人到中年后,姐姐常觉身上疼,想必就是在青少年时期透支了身体所导致的吧?
姐姐终是长成了大姑娘,在一个大雪飞扬的冬天走进了别人家的门。那时,我正在四千多里外的东北上大学,天寒地坼,我不知道姐姐出嫁时是怎样的情形,爸爸妈妈是什么想法,他们是否为姐姐落过泪。后来的很多年中,我没想起来向他们问起这事,待我想起来问时,他们都已先后离开了人世,不理我了。好在,姐姐的婆家与我家同在章畈,我家在章西,姐夫家在章东,随时随地都好往来。姐夫是杨家的长子,姐姐便成了三个婆弟的长嫂,里里外外的活儿自然都得干。我不知道她是否仍像出嫁前那么累,在我的想象中,起码不用再干那些本该男人干的重体力活了吧?
出嫁后的姐姐仍时常会从章东跑到章西帮妈妈干些农活。姐姐是个闲不住的人,干活时手脚麻利、思路清晰,见不得别人磨磨蹭蹭、摸不着头绪的样子,否则,她会唠叨个不停。因此,姐姐跟妈妈少不了时常拌嘴,自然,每次都是妈妈获胜,姐姐闭口不言。她们母女俩几十年都是如此,也不烦,更不疏离,随着年岁的增大,母女亲情竟愈发地浓了。
给姐姐最大打击的,是姐姐的小儿子、我的小外甥。姐姐有两个儿子,生得都白白大大,一表人才。遗憾的是,小儿子患有先天性白内障,半岁时曾来信阳做手术,结果无功而返,院方给出的答复是孩子麻醉不过去。我们都没多想,很快便医院手术。这一次,手术是做了,可是白内障做得不太干净,以至于孩子后来的视力仍不太正常。更为严重的是,孩子的大脑受到了影响,智力受到严重影响,二十多年来,孩子都是在章畈家里度过的,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我猜测,可能是孩子当年在信阳做手术那次没能麻过去的麻醉所导致的吧?那时,我刚在信阳上班不久,医院是我寻找的,小外甥出了那样的事,我自然愧疚自责,后悔不跌,可我自责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艰难最后都落在了姐姐和姐夫头上,他们推无所推、卸无所卸,唯有承受,只当是命运的安排吧。
时光在不经意间悄悄地溜走了,一溜就是一二十年。那期间,姐姐去东莞的电子厂做过工,也去宁波的饭店端过盘子,后来把家也从章畈搬到了光山县城,她也终于熬到了大儿子结婚的日子,熬到了乖巧的小孙女的出生。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姐姐的眉头舒展了一段日子。
不久,一个巨大的打击便突然降临。三年前的初秋,一辈子争强好胜的妈妈去世了。姐姐和我们兄弟三人都悲痛欲绝,成了没妈的孩子。还有一点让姐姐难以承受的是,妈医院里溘然长逝的,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那会儿姐姐正在家里忙着当晚的饭食。安葬了妈妈,小弟便在酒后抱怨姐姐没有尽到照顾好妈妈的责任,拿姐姐撒气。这话无疑是在姐姐流血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姐姐为此哭了好多次,却于事无补。谁能理解她痛苦的心情呢?
妈妈的离世给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因此而觉得失去了根,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再也回不到故乡了。妈妈不在了,好在我还有姐姐,长姐如母,姐姐比妈妈在世时更加关心我们了。她时常对我说:“咱妈不在了,咱们姐弟四人一定要好好的,不能让外人看笑话。”她说,最让人省心的是大弟,最不让人省心的是小弟,最让人牵挂的是我,她叮嘱我们要团结如一、互帮互助。这些本该从我嘴里说出的话,却从姐姐嘴里说出来,让人十分惭愧。一个人时,我常在心里说:“姐,你放心吧,我们都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你不用太担心!”
姐姐年轻时透支身体的恶果,渐渐地显现出来了,而且十分严重。就在她的大儿子结婚的那天下午,很多客人还未散尽,姐姐竟然毫无征兆地突然晕倒了,不省人事,在人们的大呼小叫之下才渐渐地缓了过来。此后两年间,她又多次晕倒过,每一次都惊心动魄,幸而都活了过来。去年冬的一天,她跟两岁的小孙女待在家里,她再次突然晕倒了,吓得小女女哇哇大哭,还说要拿手机打警察电话。事后,姐姐感动地说:“我那时有意识,就是动不了。听着小孙女的话,我的眼角都流出了泪……”
更让人放心不下的是,姐姐晕倒时还长长伴随着身体的麻冷,后背冰凉,仿佛敷了冰块一般。盛夏时节,别人吹空调,她还要穿夹衣,冬天就更不用说了。盛夏的一天我回了独山老家,去光山县城看望姐姐,姐姐身穿小薄袄炒菜做饭,丝毫没有热的感觉。饭后,她让我摸她的后背,果然冰凉若潭,透着一股寒气。医院里检查,没有查出结果,姐夫医院检查,也无定论。医生说,这种症状可能跟人的情绪有关,建议病人要保持畅快的心情,不要激动。
我很为姐姐的这个毛病担忧,却是无能为力,能为她做些实事的,只有姐夫。我们只能劝说姐姐别太操心,保持心胸豁达,不要想太多。很多事情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操心、发火也无济于事,不如彻底放下,让生活轻松一些,风轻云淡。姐姐嘴上应承着,估计心里还是放不下吧?
眼前堆着那么多的责任和义务,身为妻子和母亲、儿媳和婆婆,我的姐姐怎么可能做得到全部放下呢?况且还有我们三个时不时给她添堵的弟弟。
十几天前,远在东莞打工的小弟又酒后闹事,搅得一大圈子人不得安宁,我为此十分难过,我更怕姐姐的心理受到刺激而影响到她的身体。那个傍晚,我给姐姐打去了电话,安慰她说,小弟酗酒已不可救药,不用生气,好好保重身体才是要务。姐姐说没事,就是心里特别难受。我懂姐姐,可是,妈妈在世时对小弟都无可奈何,妈妈不在了,她这个长姐又能如何呢?
日子一天一天地翩然翻过,我也在人世间孤独地前行着。每次想起远方的姐姐,都能触发我的感伤和喟叹。从闪过的一道光影里,能窥视出我和姐姐小时候的样子,即便世事沧桑,我们都不再是往日的模样;从惊起的一声鸟鸣中,能倾听到姐姐在远方唤我的声音,即便相隔千里。漫步星夜,仰望空中小船似的弯月,总能乘坐那只轻盈的月亮船穿越到幼年时跟姐姐一起看星空的场景,也静观着姐姐后来常当笑话讲起的一幕画面——
小时候,姐姐带着我去邻塆捡粪,邻村的人指着我对姐姐说:“你妹妹真漂亮!”姐姐气鼓鼓地说:“他是我弟弟,你要不信,让他脱裤子给你看!”我紧紧地捂着裤子不松手,脸羞得通红……
岁月斑驳,往事如昨。在这个莺飞河唱、万木葱茏的初夏的日子里,絮叨一些陈年旧事,远在东海边的姐姐,该有着怎样的感慨呢?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三日于信阳
姐姐
姐姐比我大三岁,小时候也比我高半头;圆圆的脸庞上,一笑便显出两个小酒窝;小小的鼻翼两侧,几点雀斑若隐若现。她的眼睛里总涵着温和的光,脑后挑起两支快活的羊角辫。她对我好时,恨不得把我托在掌上,可她生气时,眼里便噙满泪花,常常骂我“该死”。
还在我脖子上系着红领巾时,姐姐便已为妈妈分担繁重的家务了。以后,她上高中,我上初中;没等我上高中,她便辍学了;待我考上大学,她已在田间劳作整整五年了。
那时,姐姐才十七岁。
每每谈及往事,她便无限神往地说:“那时,我们班考上高中的才六人,我考上了高中。”她的嘴角挑着淡淡的笑意,两眼深深地凝视着远方,沉浸在无边的回忆之中。我知道,远方有她的没有实现的梦想。
二十年多前,农村实行了连产承包责任制,每家每户都没日没夜地劳作于田间地头。爸爸教书常年在外,我们家五口人的田地就指望妈妈一个人耕作,妈妈实在忙不过来。姐姐每次放学后都要跑到田畈里帮妈妈干活,虽然她个子小,但她手脚麻利,连脾气不好的妈妈也常在背后夸她。
一个周末的下午,放了学已是六点多。姐姐牵着牛,带上茅镰和绳子上山了。一会儿,爸爸从学校回到家,我们从八点钟一直等到十多点钟,才见姐姐牵着肚子吃得圆滚滚的水牛,背着青草,一瘸一拐地走进院门。脸青了,额头在流血;衣服破了,浑身沾满泥水。原来,姐姐上山后,将牛抛牧一边,开始割草。及至天擦黑,她已割了一大捆,抬眼望去,却怎么也找不见牛。天色越来越黑,她也越来越焦急,不小心竟一下子从山上滚下去了……后来,她终于在山下的河沟里找到了正在洗澡的水牛。
妈妈心疼地拉过姐姐,轻轻地替她擦着脸,责怪说:“你咋这么不小心呢?摔死了怎么办?”话语里充满了爱怜。她找出一套干净衣裳给姐姐换上,一家人才开始吃饭。爸爸猛抽了一阵子烟,忽然阴郁而坚决地说:“从明天起,秀霞别上学了!”
秀霞是姐姐的名字。姐姐的身体猛地一颤,怔住了,而后吧嗒吧嗒地往嘴里扒着饭粒,无声地流着泪。昏暗的灯光把她的身影投在墙上,瘦弱的身影似夜风中的树叶一般摇曳……
以后,姐姐的长辫子剪成了齐颈的短发。春天,跟妈妈一道割麦栽秧;盛夏,跟妈妈一道锄草薅秧;秋季,跟妈妈一道割谷打场;寒冬,跟妈妈一道耕地缝衣。她曾因挑不动粪水落过多少泪,肩膀磨破了多少皮,没人不啧嘴;她曾累倒在收割的稻田里,昏厥在回村的小路边,没人不同情。每次收工回来,她尽管腰酸腿疼、恹恹无神,仍坚持淘米做饭,而没人知道她有多少顿粒米未进。出工时,仍要强打精神,一步一步地走向田野。耕田种地挑草头,几乎全落在弱小的姐姐身上,姐姐白皙的面庞渗进了风雨的颜色,我再也很少见到她那甜甜的酒窝了。至今,她还时常腰疼。
那时,她才十七岁!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一转眼,十年过去了。整整十年,姐姐都是在极度劳累中走过来的。每每想起往事,她便会说:“我学习不好,也只能下来劳动。”言语中饱含了多少辛酸和无奈,没人数得清。而每当我无意间在她面前炫耀我如何如何学习好时,她便睁大了那双美丽的杏眼,明亮的眸子熠熠生辉:“我要是继续上学,我也能考上大学!”
然而,那种明亮的光焰只持续了一瞬,就再也不曾闪现出来。她又默默地做她的事了。
一个冬天的傍晚,姐姐将打了几个月的毛衣亲手穿在我身上,我猛然发现,她的手是那么壮实,那么粗糙,且皴了一道道细微的裂口。我心头涌上一种难言的滋味,觉得她牺牲了太多太多……
几年后,我上大学去了千里之外,姐姐在给我的书信中动情地写道:“弟弟,读着来信,我热泪盈眶。我只望你努力学习,不提我的事……”
再以后,姐姐结婚了,有了孩子,她便将全部身心都扑在了孩子身上。
我大学毕业那年,春节前夕回到乡下老家,却没见到姐姐。妈妈告诉我,秋收之后农村活少,姐姐跟别人一块去广东打工了,过年也不回家,留下刚满两岁的孩子。她拿出姐姐寄回的信展给我,秀丽的字迹好熟悉:
“……初来时,我每天都要哭上两三次。我在电子公司里,白天至少工作十个小时,晚上还要加班。妈妈,无论家境怎么不好,您也别让小弟出外打工,在外面太艰难了……
姐姐,已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打工妹了,而她硬是咬紧牙关又一次挺了过来。
也许,姐姐生来就是吃苦受累闲不住的命。她的第二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得了先天性白内障,由于半岁时做过一次手术不太成功,不光孩子的眼睛一直看不清,手术时的麻醉药还损伤了孩子的大脑,影响了孩子的智力发育,钱花了不少,仍没治好。农民的收入太低,生活太苦,繁重的生活压力加上孩子的事情,姐姐真是操碎了心,她比同龄人格外显老,可她仍是没有想自己的事,三十多岁了仍不得不跟姐夫一块出去打工。
大学毕业十年后,我也从家乡小城流浪到了北京,成为北漂一族,才完全品尝到了打工的滋味,何况姐姐是个农民,没有多少文化。
不久前,我在北京的办公室里突然接到姐姐从宁波打来的电话,她说她在一家公司里给人家做饭,感觉挺好的。她嘱咐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不能太俭省了,以免弄坏了身体;春节临近了,有时间就回老家过年,看望母亲。我知道姐姐的心思,父亲去世快四年了,弟弟和弟媳都去广东打工了,家里只有年老体弱的母亲,带着一个年幼的小孙子。听着姐姐的声音,我不禁鼻子发涩,潸然泪下……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姐姐提着一个大红的包袱下了车,一头扑进我们中间,笑得满脸泪花,小酒窝儿好甜,好甜……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九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林平,河南省光山县人。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诗刊》《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多次获全国性诗歌、散文、小说大赛奖。代表作有诗歌《借口》《故乡的麦子熟了》《夜过黄河》、散文《回不去的故乡》《山中听水》《行吟》。出版散文集《菱角米,葵子仁》、诗集《月亮河》《我这样爱你》《幸福路上》。著有长篇小说《逃离北京》《伤城》《立地成塔》《红房子》。
赞赏
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