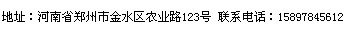青春北大荒文选3梦一般的工
一初来乍到
随着时光的流逝,四十几年穿梭而过。作为知青的我已步入老年的行列,也到了喜欢回忆往事的年龄了。过去的时光,似影视般地在脑海里展现!那是一段漫长、曲折并布满荆棘和炼狱之火的人生路。我们可以忘掉荣誉,忘掉金钱,忘掉人生的得失,但没有理由忘却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和苦难留给我们的种种铭心刻骨的记忆。
年3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恶战了。那时,我还在虎林迎春的4师33团七连,即最初下乡的地方。我和班长都说要当兵。那时不到十六岁的我,做梦也想到前线去当兵,那怕是给我们的战士送给养也行。那才叫刺激,才算真正的战士,但却遭到了拒绝。到了兵团,没当上兵,我感到有些失落,还真有些受骗了的感觉。其实,自己当时什么也不懂,幼稚得很,对一切都很迷茫。
这时,新建6师62团开始报名,需要调五十名女同志。我们团已于去年12月去了五十名男同志。我听后很高兴,就和中学同班同学张凤荣商量,她也想去。我说那还磨蹭啥呀,走吧,就到连部报了名。其实,自从来到33团七连,时间虽然短暂,但我并不安心,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这里不是我下乡的最终目的地。还真出乎我们意料,很顺利,时间不长就批下来了。即将走向新的岗位,真是十分地向往。我想,那里一定离前线更近,说不定那里的兵团战士也能到前线去呢?我兴奋地准备着出发。年的3月15日,我们又一次背起极其简单的行装,乘着解放牌卡车,向着新建6师进发了。一路颠簸,一路风尘。透过篷车的缝隙,看到荒原上厚厚的白雪。时而路过一个农场,时而出现片片森林。特别是北大荒那耀眼的白桦林,树干上的斑点如同一双双大眼睛,在目送着我们这些远去的知青。白桦林在太阳白雪的映照下,显得更加洁净和华丽。半路遇见很多解放军军车,里面坐着伤员。有头部受伤的,有胳膊受伤吊着的,都打着厚厚的绷带。战士们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本,怀里还是紧紧地抱着枪,也不知是从哪个前线下来的。我心里更加激动了,好啊,离前线更近了!我盼着早些到达目的地。
傍晚四点左右,卡车驶进了62团驻地。我看到有人从帐篷里钻出来,带着白围裙,一只手拿着盆,一只手拿着擀面棍使劲儿敲打着,欢迎我们的到来。大家也朝着他们招着手,心里有种亲切感。听车上一个带队的喊:“姑娘们,到站了,下车吧。”大家掀开卡车篷布,拿着行李,一个个跳下车,看到路边站着不少来欢迎我们的人,喊着欢迎!欢迎!仔细打量一下四周,有几顶绿色的帐篷,没有房子,厚厚的积雪中清理出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儿,再也见不到别的了。心里直打鼓,难道这就是我盼望的62团工程一连吗?怎么连房子都没有,都住帐篷?前线在哪里?战斗在哪里?当时那么多人都说了什么,我一概没听见。这时一个人讲话了,说是陈连长。也不像啊,一位穿便装的、有点儿驼背的瘦老头,矮矮的个子,黑红的脸颊露出沧桑,笑的时候露出微黄的牙齿。连长讲什么我还是没听清,就看大家都进了帐篷。我也就跟着进去了。哇!这也能住人吗?一顶长30米的棉帐篷,里面两个油桶做的炉子分别摆放在两排通铺中间,上面一个粗粗的铁皮烟囱,炉子里面烧得通红的(木头柈子)。两侧是用8-10公分粗的杨木杆子搭成的通铺,木杆上面铺着厚厚的干草。我惊讶地看着这出奇的“床”。这就是我们的床?这时一个年龄稍大点的上海姑娘说:“我是你们的班长,我叫俞根珠。大家别愣着了,自己找个位置把行李铺好吧。”我随手就把行李放在靠帐篷边的地方,有几个比我大几岁的上海知青帮我铺好“床”。我坐在床边儿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愣愣地看着帐篷内的姑娘们忙碌着。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住这样的地方呢。坐了一天的车,又冷,又渴,又累。嘴唇都裂口了,一丝血从口子渗出。真想喝点热水,可是却没有水。这时有人告诉我,没有井,所以就没有水,只能在炉子上化冰块,要么就含块冰在嘴里吧。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饭端到帐篷里。我一看是馒头,水桶里的菜汤是猪内脏炖黄豆。看到这菜我感觉恶心,一口没吃。因为我在家时就不吃猪内脏,只吃一点瘦肉。无奈之下,只啃了一个馒头,然后塞进嘴里一个冰块儿。我木呆呆的傻坐了一会儿,竟然要睡着了,干脆洗洗睡觉,可是到处也找不到水,才想起刚下车好像连长说没有井,没有饮用水,只有炊事班做饭的地窖门口,有一大堆从水泡子里刨来的冰块。在睡觉前,用自己的杯子装上点儿冰块放到床头,想夜里渴了可以吃一块儿。我看别人化雪洗脸,也拿着盆到外面挖了一盆雪放到炉子上化水。可是一盆雪化不上半盆水,只好先洗脸,再挖一盆化了洗脚,对付洗完就睡觉了。睡得正香呢,隐约听到帐篷外好像有孩子在哭,心想这里还有家属小孩吗?就再也睡不着了。而且,这床睡得我后背直疼。大油桶“炉子”烧的太热,烤得嗓子疼得厉害(下乡后就患了嗓子疼的毛病,我也没在意)。顺手在床边的杯子里拿了一个冰块放到嘴里凉凉的,觉得嗓子舒服了一些。帐篷边儿还是很凉的,冰块一点儿没化。我把头换了个方向,嗓子好点了,不知不觉又睡着了。这就是我到6师62团工程一连的第一天的情景。
第二天上班我就问:“这里离珍宝岛多远?咱能上前线吗?”有个老师傅回答我说:“远着呢,这里离同江,饶河县倒不远,河那边就是苏联。你也别瞎想了,到这里就是让你们开荒种地来了。”听到这位老师傅的几句话后,我当兵的愿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感到很沮丧。我又问:“这里有家属小孩子吗?我昨晚听到孩子哭。”他们说:“哪里有孩子啊?”一位老一点的班长说:“那是狼嚎声,咱们是冬天建连队,没有菜吃,只有从富锦买回来的冻猪内脏和黄豆,是咱们食堂菜的香味儿和这些猪内脏招来的狼。”听了这些话我很后怕,昨天半夜我还想出去方便呢,幸亏怕冷没出去。要是出去还不喂狼了?
我们四班是基建班。首先要为盖房子备料。第一项工作是到树林里伐木。班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反正就跟着他们走呗。树林不远,就在连队的对面,可是那雪太深了。我穿的是东北棉胶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人群后面走。看他们都干起来了,两位男知青用大锯(快马子)来回拉。我还是头一回看到这样的场景。等树要倒时喊:“树倒喽!”用喊声提醒旁边的人赶快躲开,以免被砸到。看大家干得挺来劲儿的,自己也不知道该干些啥,傻呵呵的正在犯楞呢。班长走过来给我一把小斧子,任务是把伐倒的树的枝桠砍掉。我左手拿起小斧子砍了起来,没一会儿胳膊就酸疼了。哎呀妈呀,还挺累的呢。擦擦满头的汗水,干起活来倒是不冷了。可是,活没干多少肚子倒是咕噜上了。该到中午啦,想着快送饭来了吧。这么冷的天,吃点热乎的就好了。我坐在伐倒的树干上,用小斧子砍着一个树桠子等吃热饭呢,看见一位上了点岁数的排长,手里拿了个鼓鼓的面袋子,往雪地上一放,随手拣了很多树枝,在空地上点起一堆篝火。他从面袋子里掏出个沾着面粉的方馒头,用树枝尖一戳,放到火上烤,说:“快吃吧,中午就吃这个,就咸菜(咸菜就是芥菜疙瘩)。”初来乍到的我,不敢说什么,也就跟着学呗。可笑的是,我烤了半天馒头都烧黑了,里面却还是冰凉的。也不管那么多,凑合吃了,却干得咽不下去。没有水怎么办?看有的人吃雪,我也学着吃两口,热乎的没吃着,反倒吃了一肚子凉的。脸被火烤得通红,背后却是冷嗖嗖的。对了,这可应了那句话:“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北大荒的冬天冻死懒人,这回可体会到了。冬天在户外真是冷啊,但只要活动起来就不冷,只能使劲儿地干活来保暖。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转眼到了四月中旬,天也不是那么冷了。每天下班吃完饭,也没别的事。我就坐在帐篷外吹着笛子,看着西下的太阳仿佛一个大火球,挂在那矮矮的灌木丛中,火红火红的。这时的我,什么也不想,全部身心沉浸在音乐中,手指灵活地舞动着。虽然吹得不是太好,但对于我也是最美好的时刻,想家时,就吹“北风那个吹”,一边吹一边流泪。我的笛声招来了一群姐妹,吹欢快的曲子,她们就合着曲子唱和笑;吹凄凉的曲子,她们就掉泪和忧伤。这就是我当年唯一的娱乐。
二割草
五月了,北大荒的天气逐渐暖和。杨树、白桦爆出了嫩黄色的树叶,连柳毛子都长出了新枝条。成群结队的鸟儿回来了,小时候只在课本上见到的大雁回来了。公路边上的沟渠里,出现了排成队的、黄绒绒的小野鸭。草甸子突然间变得喧闹起来。知青们总算把捂了一个冬天的大棉袄、大棉裤脱了下来。人也显得精神多了。小伙子们魁梧、英俊、灵巧;姑娘们俏丽、婀娜、轻盈。熬过了半年的冬天,春天终于来了。
五十多个漂亮的大姑娘,住在一顶帐篷内也是太挤了。天气渐渐热了,我们总不能一直住棉帐篷啊。盖房子的材料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因为想盖漂亮的砖瓦房暂时还没那条件,只有先盖简易房屋,让我们这些年轻的拓荒者们暂时有个栖身之所。盖这些简易房屋还需要大量的草,所以下一个任务就是割草。
记得我们班上海知青俞根珠班长和胡蔚青都去了。割草地点是离连队不远处一片荒凉的草甸子。班长给我们每个人发一把镰刀。因为我是左撇子,当时也没有左手镰刀啊,只好凑合着用喽。班长首先给我们讲了注意事项,还耐心地给我们做了示范。她是怕我们第一次用镰刀割伤手脚。
下乡以来,我还是头一回拿镰刀,也不会用。不过看别人咋干,就学着样儿做呗。一群漂亮的大姑娘,有说有笑地来到草地边。北大荒那厚厚的积雪,在春天暖和的日光照耀下慢慢地消融,露出了被积雪压了一个冬天的枯黄的野草。那草长得宽宽的,黄叶两边还带着如锯齿般的毛刺儿,不小心就会扎手。班长说:“大家开始干吧。”我们刚刚把手和镰刀伸向目标,“呼啦,嗡”一声,成群的蚊子顿时扑面而来。可不是嘛,首先人家没有去侵犯你们,舒舒服服地趴在自己的“家里”享受暖暖的日光浴呢,你们这些小丫头片子干嘛来侵犯呢?送上门儿来,那我们可就不客气喽。顿时,我们个个儿脸上、手上被这些“主人”咬得到处是疙瘩。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可都是脸一戳能冒水儿的大姑娘啊。那些小畜生可逮着美餐的机会了,用它们那尖尖嘴扎到你皮肤里,甜甜的血就进到了它们的肚子里。一会儿它满意地,美滋滋地,唱着歌飞走了。北大荒的蚊子还不止一种呢。有大的,有小的,还有身上带花儿的。你们不知道吧,这种带花儿的咬人可厉害着呢。要是被它咬了,好多天都痒得难受极了。早晚你把疙瘩挠破了,还得掉一小块皮,挤出毒水来,结痂儿才会好。后来大家有了经验,戴上防蚊帽,戴上手套,这样就好很多。另外也不敢太晚下班,因为太阳一落地平线,那些该换班的小咬就上班了。小咬比芝麻还小,防蚊帽也无济于事。小咬会从小孔钻进防蚊帽里咬你,把嘴唇,眼皮咬肿,特别难受。有的还会在你喘气或者说话时钻进你的嗓子眼儿里,咳还咳不出来,只有咽下去吃了它。记得有一位叫张耘的上海知青,在割草时,一只草爬子不知不觉地钻进了她的裤腿里。下班后她就觉得小腿有点儿疼,撸上裤腿一看,吓了一跳,只见一只扁扁的小虫子,撅着屁股,头咬着了皮肤在吸血。我们不认识那到底是啥虫子,有经验的老同志赶快告诉她千万别拉它。硬拉的话,虫子的头部会断在皮肤里发生溃烂。只能用火烫虫子的尾部,它就会自动退出来的。有人点了一根烟,用烟头烫那虫子,它果真慢吞吞地从皮肤里退了出来。仔细一看,是一个圆扁型的虫子。这种虫子吸血更厉害,而且还会钻到皮肤深处。太可怕了,从那以后,我们只要上班,都要用绑腿布把裤腿扎紧。
千百年来,生长在这片荒原上的草,虽说不是太高,双脚踩在上面感觉软乎乎的像席梦思。下面的草根用铁锹挖出,竟有30-40公分厚。可想而知这草原有着多少年龄啊。割草的活还真是累人,也不容易割。因为这些荒草整个冬天被厚达50公分甚至更厚的雪覆盖着,本来很坚强的草都被大雪压得服服贴贴的,不能抬头挺胸面对蓝天,而是趴倒在地上了。我们先要大弯腰或蹲下,用镰刀先把草搂起,手抓住后才能割下。好在我就割过这么一次草,确实是考验我们的忍耐力呀!
我拿个右手镰刀,只得反着用。这样一来经常会割到鞋,因为刀会往上滑。就这样还是坚持下来了。姑娘们把割下的草打成捆,堆成大垛,等待大车拉回连队。回头再看让我们收拾完的草地,真像似被剃了寸头,只剩草碴了。还有那新长出来的嫩嫩的小草。它们昂首挺胸迎着朝阳,茁壮成长着。
三盖房子
我们工程一连主要负责给团部盖房子。漫长的冬季总算熬了过去,盖简易房子所需的木料和草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下一项任务就等着盖房子。
我在33团七连时看到过马架子,就是当年老铁道兵开发北大荒时住过的那种。现在我们要告别帐篷,住上自己亲手盖的房子,可就是不知要盖啥样的“简易房子”?基建班,大家都叫瓦工班,我们就成了泥瓦匠。我们工程一连下属有木工一班、二班、瓦工班、备料班(也就是干杂活的班)、后勤班以及食堂。
最先盖的是“草皮子房”。正式开工了,班长范殿生把各自的工具发下来,注意事项等罗嗦一会。给我发一把平板铁锹,先把简单的地基挖好。这地基太好挖了,全是厚厚的草皮子和油黑的黑土层,再往下就是白浆土了。因为白浆土层比较硬,地基要挖到硬土层才牢固。木工把伐来的二十多厘米粗的木料去掉树皮,去掉疙瘩,分别埋在四个角。在地基上面搭好房架子,用细点儿的木杆,隔一段架一根。这些活是木工班的工作。木工干完后,他们就又开始做下一个房架子去了。下面该我们瓦工班上场了。先在旁边找一片很平的草地,把上面的荒草铲掉,露出黑土和草根那层,用平板铁锹把草皮子切成长六十厘米,宽三十厘米,厚二十厘米见方。然后再把切好的草皮块儿像砌砖墙一样砌到地基上,一层一层整整齐齐码好。待草皮子墙稍有点干,再把墙里墙外抹上碎草和的泥巴,房子就起来了。最后再在房里铺上木板,或整齐地摆上细杨木杆子,上面再一层一层铺上我们割来的草,这就是通铺的床了。这叫“草皮子房”,也是我们连第一栋简易房。但是这种房子时间长了,草皮子中间的水分很容易干的,那么墙面就有空隙,冬天就不保暖了。北大荒的冬天气温在-30℃,这种临时房子是无法过冬的,真不如棉帐篷暖和。第二种房是“拉合辫儿房”。地基是一样的,房架子也是由木工先架起来。首先在旁边空地上挖个大坑,深度也有一米多,再往坑里放很多水和土,人脱了鞋,挽起裤腿儿下去,用脚把土和水搅拌成泥浆(真凉啊)。把割来的草缕成左手一把,右手一把,再把左右手两把草相交拧成个结,递给池子里的人,放到泥浆里扭成个泥辫子,再递给上面的人,把泥辫子编到房架子上。这种房架子和别的不太一样,中间的木条多,便于编草辫。一层一层地编到够房子的高度,待稍干一些,再把两面墙抹上泥巴。房顶和前面草皮子房相同。这叫“拉合辫儿房”。不过这两种房子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墙泥巴就都掉了,还有就是潮湿。
第三种房子是“干打垒房”。地基和房架子跟草皮子房一样,但墙可实在多了。那是用两块厚木板固定在两边,然后挖土往木板中间装,装一层土再用大木锤子使劲夯,砸得越实越好。一层一层地装土,一层一层的砸到墙够高度以后撤下木板。墙的厚度有四十多厘米,两面还是抹上泥。这叫“干打垒房”,比“草皮子房”和“拉合辫房”要好得多。挺结实,还保暖,寿命也要比前两种房子长好多。
有了房子,老鼠也有了窝,不用再野外打洞了。有吃有喝,老鼠个个都肥头大耳的,大摇大摆地在房子里安家了。被子里成了老鼠的产房,又软又保暖。一次我想上床睡觉了,伸手放下被子,却抖落出一窝粉红色老鼠崽,吓得我眼泪都出来了,心里麻酥酥的。这还咋睡觉啊,怪恶心的,只好马上拆洗被褥。到了阴天下雨,屋里地上可就成了泥浆喽。那蚊子就不用再提了。这些小东西陪伴我们十多年,没得上疟疾算万幸。
年7月,开始给团部盖真正的房子了,是砖瓦结构的机关办公室、广播室、商店、宿舍等。给团部盖砖瓦结构的房子,需要很正规的设计。那时候全团也没有一座烧砖的窑,那些砖瓦都是从同江拉来的。
首先是挖地基,要求挖一米多深,宽五十公分。把我们从山上拉回来的石头敲成橄榄球大小,再把这些石头填到地基里,用四连拉来的沙子拌水泥后,一锹一锹均匀撒到地基里,然后挑水挨着倒,这叫灌浆。灌浆的水是我们到一里路外的水井,一担一担地挑到工地的。一个上午,我大约挑三十担水。肩膀先是压红,然后肿了、破了,穿衣服都磨得疼,晚上肩膀痛得睡不着,全身好像不是自己的,不听使唤了,总算坚持到地基打完。
地基打完了,下一道工序是砌墙。范班长让老徐师傅带几个男知青和我上墙砌砖,并每人发一套砌墙工具。什么瓦刀,大铲,线坠等。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上墙砌砖是大工,在下面和泥,递砖是小工。女的就我一个是大工,其余全是男生。这还真是一项新工作。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砖瓦房是怎么砌起来的,真得虚心向老师傅学呢。
有位男知青私下里嘀咕说:“班长怎么不让我上墙啊,却让女孩子上墙砌砖,能一只手拿砖吗?能拿得了瓦刀吗?”班长也挺有意思,非让他给我当小工,他好大的不愿意呢。我们一个人负责一个墙垛。我记得很清楚,右边是上海知青傅伟良,左边是天津知青梁雨田。他们似乎都干过,熟练得很。他俩给我做示范,怎样错开砖缝。范班长耐心地给我讲要领,老徐告诉我怎样往砖上抹泥。一手拿瓦刀,一手拿砖,用手翻转砖挑选光面时,我的手小,拿不住砖,几次砖掉下来砸到自己,或是把一块好砖给摔碎了。一天下来,手脖子疼,手指肚也疼,胳膊痛得抬不起来。但是,还是那句话:坚持干!
砌墙可是个技术活。看准线,泥抹匀,抹泥中间还要留点空隙,砖放正直,砖之间的缝要错齐。别看我是第一次,可认真呢。那个时候,确实人人都很认真对待自己所干的每一项工作,绝对没有豆腐渣工程,也没地儿找回扣。范班长还夸说:“小刘干的不错。”至今,我还记得哪个墙垛是我砌的呢。
在砌最高处那个山墙时,小工给我用木锨往上扔砖都是两块一扔,我就得两块两块地接。手套大又戴不住,又怕戴手套接不住掉下去砸到人,只能不戴手套接砖。没有多长时间,手指肚都磨破了,钻心一样地疼。我的小工方世俊跑回连队,到卫生所要来胶布给我缠上破了的手指继续干。其实不光我是这样,好几个人都是磨破了手,没有一个人叫苦或怠工。这就是知青,知青精神。
墙垛全都起来了,房梁房盖也都顺利完工,房顶上也上完了红色的瓦。抹内墙时又发了一个大木头板抹子,是打平墙面用的。剩下的工序是抹窗户框。班长又发给我几样小工具,小巧玲珑,看着挺好玩的。班长说:“别光看好玩儿,我是看你干活还挺细。你先听我教你怎样抹窗户口。”他慢慢地给我做示范,教我抹窗户框,我给班长扶着模板。这真是个细致的活。班长给我扶模板让我抹。他看我抹得还挺好,每个角抹的都挺直,就放心地到别处指导去了,让我的小工方世俊给我扶模板,上泥。
到了年底,除了武装连还住帐篷,老职工和家属住干打垒房,其他人都住上了我们自己盖的砖瓦房。我呢,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城市小姑娘,学会了这么多本领。苦啊,累呀,也都坚持过来了,当时,还觉得还挺美的呢。手上磨出了很多老茧,再也看不到下乡前那双白嫩嫩的小手了。
从我不到十六岁来到北大荒,在兵团工作了十一年。我在62团工程一连工作了两年多,这里记录的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片段。这两年很苦很累,但又是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写于年12月31日
修改年11月29日
作者简介
刘淑琴,女,年12月19日生。
年-年小学。
-年就读于黑龙江省鸡西市第八中学,68届初中生。
年11月9日下乡到4师33团七连,农工劳动。
年3月调到新建6师62团工程一连,食堂、基建盖房子工作。
年调往一连,做农工,食堂工作。
年3月调到新建三十二连,先是农工,四月后调到机务联合收割机手。
年任车长。鸡西来我团招生上大学,有我的名字,但领导告之:机务人员团里不放。我无奈,后因关节炎,无法在机车上再做。
年我又返回一连,看座机发电,后做刨床工作,直到返城。
年2月返城到河南省舞阳钢铁公司;剪板机操作员,开叉车,发货员,统计助理,兼判定员,劳资员,直到退休。
(责任编辑晓歌)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