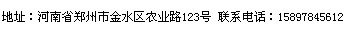小说连载大漠祭13
第十三章21
二舅笑道:“北斗主生,南斗主死。你没见牌位上的那几个字吗中天北斗解厄延寿星君,北斗能解厄,能延寿,主生。”老何说:“有个孝子,命尽了,还在犁地。吕洞宾变个道人去点化。远远地,孝子就扔下牛鞭跑过来,笑着说,老爷爷,我身上只有这点钱,要不你等一等,我到家里去取。吕祖说,你明日午时必死,还犁啥地呢张生急得哭起来。道人说,今夜三更,华山上有两个老汉下棋。你带壶酒上去,不要说话,跪一旁,等他们喝干杯中的酒,你就斟上。等他们喝了你的酒后,你就求北边的老头儿,叫他给你加岁数。吃了人的嘴软,他一定加。张生就上了山,真见两个老汉下棋,就跪下,就斟酒,就求寿。老汉骂吕洞宾多嘴,只好将张生的岁数从一十九岁,改为九十九岁。哈,从此,人们才知道北斗主生,南斗主死。”“说是那么说,谁见来”老顺笑嘻嘻丢一句,打发灵官去厨房里看看鸡肉炒熟了没有。“啥东西都是信则有,不信则无。”老何笑道。灵官端上了炒好的鸡肉。老顺笑道:“来呀。管他谁主生,谁主死。我们吃我们的。活一天吃一天,吃饱喝足,哪天主的人不叫吃了,再说。”众人笑着洗手,吃肉,喝酒。12次日忌门。照例忌三天。老顺在庄门上吊了个红布条儿。一忌家亲引来外鬼作祟。庄门上本来有门神值班。死去的家亲可自由出入。当不学好的家亲引着鬼友上门做客时,门神只好放行。所以,家人被外鬼伤害的话,家亲多半是元凶。平时逢年过节祭祀先人的主要用意就是求家亲保佑自家子孙,驱走不怀好意的鬼,更别领外鬼来家中做祟。家中祭神时,必须请家亲,外鬼也会不可避免地混入。所以,仪式结束后必须打醋弹。不论好坏善恶,尽数轰出。而后在庄门上吊个辟邪的红布条,即使门神碍于面子不好意思阻挡家亲,能辟邪的红布条也能将一切鬼类拒于门外。二忌外人,尤其是忌阴人。阴人者,女人也。女人阴气重,更有人世间最脏的能叫人倒霉的东西月经,就更必须“忌”了。所以,吊个红布条,告诉人们:今日忌门,谢绝入内。因为忌门,屋里显得很冷清。喜欢在“红火处卖母猪肉”的猛子早就耐不住了。他百无聊赖地翻几本武侠书,正想找个理由往外溜,却听到有人喊庄门。猛子透过门缝一看,原来是白福和兰兰,牵着上次来“盖”骡子的那头驴。猛子就问老顺开不开门。老顺很为难,一来说好忌三天门,不叫外人进。兰兰也是阴人,又挺个大肚子,更是“阴”得厉害;二来,白福牵了驴来,定然是上回没“盖”定,又来找魏没手子的。老顺知道祭神是大事,听说古人还要斋戒沐浴呢。正犹豫,却听得老伴说:“开门,开门。丫头女婿又不是外人。忌门哪有忌自家人的”猛子就去开了庄门。看到兰兰顶个大肚子进门时,老顺的心顿时阴了,想,这神又白祭了;但他只是嗯一声,应了兰兰的问候,就出了庄门。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对白福说:“上回没盖定”听到肯定的答复后,便叫他牵了驴跟他走。清闲了几日的儿马一出圈门,就咯叽咯叽叫起来,扬蹄,喷鼻,把它的阳刚之气显露得淋漓尽致,搅碎了魏没手子家相对的宁静。一见到白福家那头美丽的草驴,儿马便一次次直立,想把前蹄搭到对方背上。黑草驴则拌动着嘴,口水哒哒流下。
第十三章22
魏没手子用力拽缰绳,以防它情不自禁,做出无用之功。老顺道:“你这次用点劲,一下盖定,叫人家一趟趟跑也不是回事。”魏没手子笑道:“你那么急,干脆你给一脚盖定算了。”“哪能呢劁猫儿的不骟猪。你天生是盖牲口的。”却听得身后传来笑声。老顺一看,是五子。听瘸五爷说,医院出来,五子规矩了许多,很少追女人,夜里也安稳了许多,便问:“五子,笑啥哩”五子不答,直了眼瞅驴。老顺觉得他眼神不对,但又说不出哪儿不对,便戏说一句:“想媳妇了”不再管他。魏没手子的任务是将儿马的热情引入正道,使其单纯的泄欲变成繁殖力。这个过程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他只须将那个横冲直撞的物件扶正,使其到该摩擦的地方摩擦;复杂的是,牲口中也有些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货色,它们总要真真假假地跳弹一番,不让那双“脚”轻易地“盖”到自己背上。这就需要魏没手子耐心的诱导。他用各种方式撩拨,诱出其生理的本能战胜心理的羞涩。但也有个别视贞操如命的贞驴贞马,会顽强抵抗,会用自己的铁蹄给胆敢亵渎它的儿马以狠狠的惩罚,踢掉它的欲火,踢垮它的信心。这时,魏没手子便要设法增强儿马信心,使其重振旗鼓,同时,将“贞”牲口牵进那个能叫公方随意动作又不叫母方施展手段的特制木笼里,帮助前者强*后者。只是这“强*”表现虽恶劣,目的却高尚,是为繁衍子孙而不是单纯泄欲,魏没手子自然无一丝惭愧。白福的草驴才三岁,没怀过驹,若没有上次的性经验,便算得上不谙世事了。也许上次儿马不会怜香惜玉的粗糙动作使它仍心有余悸。因此,当儿马那不太温柔的双“手”“盖”到它背上时,它先是吃了一惊,而后便羞恼地踢了对方几脚。忽听五子大叫一声。儿马犹豫不决了。但显然,因对方的不轻易就范,使它更加心痒难忍欲火中烧--看来,吊胃口不仅仅是人类的专利--虽说它已从对方下流的口水中看出了其心思,但还是不敢冒然造次了。在魏没手子“跳--跳--”的吆喝声中,它转着圈子,打着响鼻,时而“咯叽--咯叽--”叫几声。终于,儿马鼓足勇气,长嘶一声,立个蜻蜒,双足落在了草驴背上。草驴却出人意料地显出听天由命不与你计较的样子,很快却又疯了似蠕动嘴巴,成一副乐不可支的贱相了。五子早不笑了。他痴痴地盯着工作的儿马,脸涨得通红,鼻孔大张,出气声很大,很促。眼里充血似的,泛出骇人的红。忽然,他再次大叫一声,用尽全力,不似人声,仿佛要把胸腔中激荡的某种东西吼泄出来。他扭曲的脸上显出痛苦至极或是快乐至极的表情,充血的眼里射出被激怒的野兽才有的光。五子的目光转向了正和灵官朝这边走来的兰兰。他扑了上去。老顺撇了缰绳,叫:“五子--五子”兰兰还没反应过来,已被五子紧紧抱住。五子咬着兰兰的嘴。那真是咬。兰兰发出骇人的叫。五子边咬边将兰兰拥到墙上,屁股一下下拱着。
第十三章23
兰兰挣扎着。她的力气本来大,但这时却因意外的惊吓遍身瘫软,加上五子的力气忽然大得异乎寻常,轻易地便将那反抗消解了。“呔”老顺大喝一声,叉开五指,狠狠扇五子几下。五子一撩,将老顺扔到一旁。在五子分心的瞬间,兰兰挣出了他臭哄哄的嘴。她尖叫着躲避那一次次向她凑来的扭曲的泛着红光的脸。白福扑了上去,撕住五子头发,用力后拽。五子负痛,松开兰兰。兰兰顺势逃进庄门。老顺、白福、魏没手子几人合力,才降住五子。被降住的五子很安静,像放光了气的皮袋。他只是笑,谁也不望地笑,痴痴地笑。笑茫然,目光也茫然。老顺说:“这娃儿真毁了。”便和灵官把五子送往瘸五爷家。瘸五爷意外地没有表现出惊奇。他只是应付差事似的骂声“畜生。”然后长长叹一口气,掏出烟袋,蹲在地上抽烟。五子却仍那样痴痴地笑。那份宁静,那份痴迷,很像一个思念情人的少女,一点也看不出他方才尚有野兽似的举动呢。“没啥。”老顺安慰瘸五爷,“真没啥。五子脑子有病”瘸五爷不语,长吁了一口气。老顺说:“这由不得他。医院。”“由天断吧。”瘸五爷说。灵官从五子痴迷的笑里看出他很幸福。他一定在品味着什么。他究竟在品味什么呢是品味他过去实在的恋情还是品味虚幻的想象无论哪种,他一定是幸福的了。那种痴迷的笑,既可怕,又显出一种迷醉。忽然,五子不笑了。他的眼里又泛出红光。他的鼻翼扇动着,扇出疯狂的粗大的呼吸。顺着他的视线,灵官看到了大头媳妇会兰子的影子。她正在门口和五子妈说啥。五子怪叫了一声,扑过去。会兰子还没回过神来,已叫他按在地上。五子妈叫了起来:“遭罪啊。快快,死鬼。”瘸五爷扑出,从柱子上取了皮绳,劈头盖脸向五子抽去。五子叫一声,回望一眼。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因为疼痛,他的脸扭曲了。但很快,他又扭过头去,颤动着身子去啃会兰子的脸。皮绳发出声声闷响。五子妈像扇着膀儿护小鸡的老母鸡那样前后跳着,发出惊叫,不知是在呵斥儿子,还是在阻挡老子。“老五。”老顺拽住皮绳,“行了,行了。”
第十三章24
“这个畜生。畜生丢底典脸的畜生”瘸五爷丢了绳子,扑上去,撕住五子的头发,扇了几个耳光。老顺灵官上前,撕开五子。会兰子的嘴唇破了。她发着抖,脸色煞白。五子含糊地叫着,似亢奋,又似抗议。她盯着瑟缩的会兰子,用眼里的红光和扇着的鼻翼尽情表演他的兽性。“畜生畜生”瘸五爷在院里转圈子。会兰子哭道:“叫我咋见人你说,叫我咋见人”五子妈捞住会兰子的手,带着哭声说:“求你了,求你了。可怜可怜我老婆子,行不行不”老顺对会兰子说:“别哭了。五子有病。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你又不是第一次叫人咬嘴唇。闹洞房,叫人咬成个猪八戒,也没见你掉尿水。这会儿成个婆娘,反倒像黄花闺女似的。”会兰子说:“说得倒好。你叫他咬一下看。”“人家咬吗我倒想尝尝叫人咬的滋味,可人家能看上我这胡子拉茬的嘴吗人家咬你,还不是见你的嘴好”老顺笑道。会兰子捂着嘴,进了屋,照照镜子,取了蒸笼,走了。13一进家门,老顺听老伴说兰兰被五子挤压后不舒服,怕是伤了胎气。猛子已请来大夫,号了脉,开了药方。见了老顺,大夫说:“可能不要紧。”老顺急了,这口气,咋和胖兽医老黄一个味儿“可能”“可能”是啥“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可能”不要紧,也“可能”要紧;便赶紧给大夫递了根烟,大夫又强调了一句:“没事,没事。”老顺才放下了提悬的心。一见写得满满的药方,老顺心里有些发毛:猪死折了财,祭神花了钱,现在丫头又得破费。真是倒霉。阴影和不快连接起来,水一样漫延开来,把心搅了个乌烟瘴气,就恶恨恨问老伴:“咋个伤了胎气神神道道的。”“肚子咯咛咯咛疼。”老伴不满意老顺的语气,面露不快。“贵气了她。头疼了,脑热了,肚子疼了屎憋了。你咋知道伤了胎气小姐的身子丫环的命不成那些年,你生娃娃,头一天还要抡大铁锨挖地,也没见伤啥的把她贵气的。”“也就是。这年月的人咋都贵气成这样惯的。”老伴小心地望着老顺的眼睛,悄声没气地说:“要不要请齐神婆给拨摆一下”“屁”老顺突地睁大眼睛,“你有完没完除了齐神婆,你不会放别的屁”“我是说,猪死的怪,今天的事也怪。你说五子,咋忽然总觉得有些怪,再说”
第十三章25
“再说啥”老顺发怒了,“你脑子里少乱打转转,能有个啥事”老伴红了脸,气恼地说:“好,好,我不说。有了你这句话,我不说。有个三长两短,你给交待。”午饭后,白福牵驴回去了,兰兰和引弟没走。老顺怕兰兰真有个啥闪失,落下白福的埋怨,但又不好撵她走,就狠狠出几口横气。14兰兰和莹儿到一块,就抹泪。哭一阵,兰兰才说,村上摧得紧,要交五千元罚款,才不引产。婆婆打发兰兰到娘家来求救,借几千。老顺火了:“啥借我我也剩不了四两油了。”兰兰就哭了。莹儿也哭了。引弟慢慢走到莹儿跟前,用小手给她擦眼泪。莹儿搂住引弟,哭得更厉害了。灵官妈抹把泪,粗声大气怨老顺:“没钱,连个好话也没有吗丫头轻易不来,一来,你就咋咋呼呼。受外人的气不说,到娘家也没个安闲。”老顺一听,不言语了。灵官妈劝兰兰:“想哭的话,就放开。哭一阵,心里就好受些。憋得时间长了,会憋出病来。”兰兰反倒抹去泪,说:“其实,我也知道娘家的难处。可实在也没法子了。要不然,也张不开这个嘴。”老顺长长出口气。莹儿搂了引弟,露出一丝笑,问:“还会唱我教的那些口歌儿吗”引弟说:“会。点点斑斑,草花芦芽,打发君子,出门一个。”“还有呢”“”“还有呢”“姐儿嫁到远方家,来也来不下,去也去不下。眼泪滴到胸膛上,雀娃喝上冰得慌。眼泪滴到驴槽里,雀儿喝上发嘲哩。”“行了,好了。”听了引弟奶腥腥的歌谣,莹儿眼里又溢了泪。莹儿对兰兰说:“我那个哥的脾性我知道,高帽子匠,听不得半句儿不顺心的话,爹妈都跟上淘不少气了。可真委屈了你。”兰兰笑道:“现在了,还说这些干啥”她把嘴凑到莹儿耳旁,悄声说:“你也不一样吗我那个哥哥,榆木疙瘩一个,叫你满肚子的情话也不知如何说。”“去你的。”莹儿推她一把。兰兰说:“不过,他的心可好。小时候,我赌气不理他,他就搓脑袋,转圈子,抓耳挠腮,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莹儿哼一声,想到了什么,忽地红了脸。兰兰揪住她耳朵,说:“我可不许你欺负他。不要见个油腔滑调的,油头粉面的,嘻皮笑脸的,就把哥撇了。”莹儿笑道:“不说这个了。你还是把自己管好些,不要和队里的那些二杆子嘻嘻哈哈,拉拉扯扯,最后管不住自己了。”兰兰脸红了,认真瞅莹儿好一阵,才说:“谁像你。”引弟偎上来,捞了莹儿的手,奶腥腥地说:“我好想你呀。”莹儿亲亲引弟脸蛋:“我也想我的小丫丫。”引弟说:“我有好多好多话要对你说呢。”莹儿笑道:“哟,引弟有秘密了行呀。”将耳朵伸向引弟:“好,我听着呢。”引弟晃着小脑袋说:“我不叫别人听。”就拉了莹儿,出门。
第十三章26
引弟四面望一下,悄悄说:“我买了个布娃娃,给妈妈肚里的小弟弟。”莹儿笑道:“哟,引弟懂事了。你哪儿的钱呀”引弟说:“上回你给的。还有猛子舅舅、灵官舅舅、奶奶给的。胡子白白的,长长的,尖尖的,身子红红的。我好喜欢,可又舍不得玩,怕给玩坏了。”莹儿亲亲她脸蛋:“你放心玩。玩坏了,我再给买个大的。”引弟摇摇头:“不,那是给小弟弟的。我好想小弟弟呀,妈也想。妈妈问我,引弟,这回妈生个啥我就比个小弟弟尿尿的样子,妈妈就笑。”莹儿心里一热,蹲下身,把引弟搂在怀里:“还是我的小丫丫好,多懂事。”引弟说:“还是小弟弟好。爹说,能顶门立户呢。丫头再好,也是人家的人,十个好丫头,顶不上个瞎娃子。你说,我要是娃子多好。”莹儿说:“那是他胡说。引弟多好,灵丝丝的。养个肉头肉脑的娃子,气都把娘老子气死了。哪有引弟懂事”引弟推开莹儿,一本正经地说:“这可不敢胡说的。这一说,妈妈的肚里的弟弟别变成妹妹。”莹儿笑了:“好,好,不说了。”引弟皱着眉头,歪着脑袋想一阵,说:“我可真不明白啦。爹说,上回没活的小弟弟是我刻死的。我没刻呀”莹儿沉了脸,说:“屁话。谁说的”引弟嘟着嘴:“爹爹说的。开头,我还想,我要是能刻的话,再给刻一个。一说,爹爹就打我。两个大嘴巴,打得我啥都不知道了。眼里哗哗冒火,好痛啊。”莹儿拧了眉头:“那他可就不像话了。像引弟这么好的丫丫,心疼还心疼不过来呢,哪里下得了手呢真是个榆木脑壳子。引弟,告诉我,恨你爹不”引弟摇摇头:“不,才不呢他为啥打我”莹儿捧住引弟的小脸,轻轻抚摸着:“不为啥。他是个糊涂鬼。引弟没错。不过,以后不准说刻啊刻的,听见不”引弟哼一声,又说:“那我给爹说,以后我不刻小弟弟。成不成”莹儿假装生气了,说:“不行。啥都不要说。不要说刻啊刻的,听见没”引弟不解地望莹儿,好一阵,点点头。莹儿亲亲引弟脸蛋,说:“好了,我的小丫丫。我可要进屋了,还有话没”引弟四下里望望,悄声说:“莹儿姑姑,妈说姑爹有病你要钱不我有法子”“啥法子”引弟把嘴对到莹儿耳旁说:“奶奶有钱,好多好多,在枕头里不是分钱,是票票子。我给你拿些。”莹儿说:“那不成,你爹要打死你的。”引弟说:“不怕。我长大了,挣钱还他长大,挣上钱。我还。”莹儿鼻子一酸,搂住引弟,流泪道:“我的好丫丫,心肠真好。我不要。”引弟急了:“我拿给你。我不怕的。”莹儿说:“不要,真不要拿。真用钱的话,我向妈借。”引弟说:“不行的。奶奶不借。上回,妈妈要钱。奶奶说:哪有钱呀人都穷疯了。哼,骗人。爹说,那钱不能动,交啥款的。”莹儿说:“噢,计划生育罚款。”“对,就是这个款。”“引弟,这是买小弟弟的。你拿给我,人家抓小弟弟咋办”引弟怔住了,歪着脑袋想了许久,想不出法儿,急出了眼泪。莹儿搂住引弟,任泪水流了一阵。擦去泪,挤出笑,说:“好了,小丫丫,别发愁了,你姑爹的病会好的。”引弟跺着脚:“急死人了。可真急死人了。”莹儿一把抱起引弟,脸贴脸,出了庄门,眼泪又泉一样涌了。引弟也哭了:“你说怎么办我要是猪多好。卖了,不就有钱了”莹儿抽泣道:“我不是急,我是我是我的乖乖。有你这个心,就行了。管他钱不钱的,啥都不如我娃的心。”引弟吃惊道:“啥心能卖多少钱”莹儿破涕笑了:“多少钱也不卖,多少钱也买不上。我要生下你这样懂事的丫头多好。”引弟说:“又胡说了。是娃子。”莹儿笑道:“是娃子,是娃子--其实十个好娃子也不如我的引弟。不如。”说着在引弟脸上不住地亲。引弟害羞了,脸红红的,像涂了胭脂。
第十三章27
15夜里,兰兰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老顺忽然发话了。他的声音空空洞洞的,像在说梦话。他叫了几声兰兰,说:“其实,我不该发火。可说啥,粮食是粜不成了。不然,今年得缝住嘴。你也体谅爹的苦处。”兰兰说:“我也知道的。没啥,真没啥。不管咋样,得活。”老顺说:“瞧,你又说气话了。我知道,你气恼爹。这辈子,爹对不住你。可又有啥法子事到如今”兰兰说:“爹,又胡说了。谁怪你呀不怪爹,真的不怪。”老顺叹口气:“怪不怪也没治了。活人嘛,想通点。眼睛一闭,一辈子就过去了。”兰兰说:“我知道。你也用不着太难受。没啥。真没啥。”老顺说:“我再也没别的法子,揪揪掐掐,也攒了几个。不多,二百来块。你先拿去用。谁也不知道这钱。原想防个啥急事,怕凑手不及。这也算急事。你先拿去,斤里不添两里添。再想想别的法子。我可真没治了。”灵官妈忽然笑道:“哟,你个老贼还留了后手呀。起外心了是不是”老顺没作声,半天,长叹一口气。兰兰说:“我想通了,真的想通了。不说交不起,就是能交起,也不交了。五千块,想想都骇哄哄的。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咋也行。就算抓去,也没啥。咋也是个活。听说犯人还一星期吃几回肉哩。”说着,她笑了。老顺思谋一阵,说:“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也不能把你们咋的。总得叫人活吧”兰兰说:“就是。”静一阵,老顺说:“其实,我也没有攒下啥钱。我是给你们宽心。”灵官妈笑了:“哟,说出的话,可收不回去了。拿来。天冷了,说啥,我也该缝个棉袄。那个旧的,实在不成了。里子面子都磨酥了。再穿,就成个烫毛鸡儿了。”老顺笑道:“哟,真是后悔,一句话,就把底给露了不过,说实话,那钱还是存下的好。这么大个家,说不准啥时遇个急事。事到头了,找谁去”灵官妈说:“不要一天放咒了。哪有那么多事”老顺说:“我又没说这个那个,我是说遇个啥急事。”老顺越解释,灵官妈就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总觉得会有个啥事似的。兰兰说:“也该给妈妈穿一套了。多少年了,尽是灰楚楚黑乎乎的那套。养下几个墙头高的儿子,不说别的,为了顾儿子们的面子,也该穿囫囵些。”灵官妈笑了:“说的倒轻巧。我也想阔阔穿几件,可拿啥穿拔根肋条给人家,人家又不要。算了,半截入土的人了,能遮个羞就成。还是你们年轻人穿好些。要不,明天你拿上几块钱扯块布,叫花花丫头做一个。她做的也不错呢。不要手工钱。”兰兰说:“算了,算了,我也不要。也不是没穿的。爹好不容易才攒了那点儿,谁舍得挖他的护心油啊”说着,吃吃笑了。老顺说:“你用就用去。我说是说,可在你们儿女们的身上还不抠馊。”兰兰说:“算了,算了。你的后音子里都没气哩。”“也就啊。”灵官妈接口道“谁不知道你是个啬鬼。”老顺笑道:“嘿,你们都成好人了不啬,你们咋长大的喝风啊农业社那阵子,一大堆娃儿们,就两个劳动力。不啬,早把你们喂狗了。”兰兰笑道:“喂狗倒好了。”
第十三章28
灵官妈说:“现在好多了,你们还算啥受苦。我们小时候,才叫苦。连个被儿也没有,只有一个大皮袄。清早晨,爹一去给地主扛长工,我们就得受冻。一天价饿得眼睛发昏。”老顺说:“还用得着比那个时候吗就说前几年,农业社里,日子也不好过。苦上一年,连个肚子都混不饱。现在好咧。不管咋说,肚子能混饱。人么,还指望啥哩”兰兰说:“你们就一天吃啊吃。人活着,就为了吃吗”“哟”灵官妈说,“不为吃为啥呀当然,也为穿。人活一世古来稀,就为吃穿娶个妻。还想啥哩”兰兰笑道:“那不如转生个猪呀”老顺说:“人哪能和猪比呀猪吃了喝了,就是睡,舒服得很,不愁吃不愁穿的。要不是怕挨那一刀,我还真想下辈子投他个猪。”灵官妈笑道:“你还说得稀罕,想当猪哩。猪是能轻易当的吗人家那也是修的,是上辈子修下的福份。你嘛,还是受你的苦,当你的人吧。再不安分,叫你当个牛,苦上一辈子,临亡了,还得挨上一刀。肉叫人吃了,骨头里的油也叫人熬干榨尽。”老顺说:“嗬,把人说的心里瘮怪怪的。”兰兰笑了。灵官妈说:“要说,人太对不住牛了。听说老天爷给牛封下的是一棺一椁,要很排场地发丧。人听成一熬一锅,倒给煮吃了。”老顺说:“屁。羊不也是一熬一锅吗”灵官妈说:“人说牛是菩萨转世的,活着为人服务,犁地啦,挤奶了。死了,还把啥都贡献给人了。”老顺说:“说是那么说,可谁知道因果报应个啥哩为啥现在得势的尽是恶人挣大钱的,尽是坑人骗人算计人的。受穷的,尽是本分人。”兰兰接口道:“而且,得怪病的,大多是好人。能说清吗”老顺说:“难道天也瞎眼了吗”灵官妈说:“这可不许胡说。人又不是只活一辈子。人家上辈子积了德。这辈子受福,是应该的。这辈子作恶事,会报应到下辈子。”老顺说:“说是那样说,可谁知道反正,这世道,尽是老实人吃亏。莫非,这吃亏的老实人,都是上辈子作了恶不成”灵官妈说:“我说不来。我也是听人这样说的。”老顺翻个身,出口横气,说:“不喧了,睡觉。越喧越着气。”
第十四章1
1这年的大年初三下了一场雪,气温骤然降了下来。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农民对于雪天,自然是喜欢的。隔窗望去,大地白茫茫一片。这时,偎在烫炕上,或睡懒觉,或谝闲传,边喝茶,边磕瓜子那份懒散惬意,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来看外父外母的白福却没有这份闲情。大清早一睁眼,就被糟糕的情绪笼罩了。原因是他做了个梦:女人生了娃子--是娃子,他梦里还认真地摸那个宝贝尖尖呢。忽然,一个白狐蹿过来,把娃儿叼跑了。白福大喊着醒来,把兰兰都吵醒了。兰兰问:“又怎么了”白福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许久,才说:“狐子”兰兰问:“啥狐子”“狐子把娃子叼走了就是你肚里的这个。”白福觉得喉头很干。兰兰笑了:“尻子没有盖严。”白福闭了眼,回忆那个梦。忽然,他发现梦里的那个狐子竟是他几年前弄死的那个,心里一激灵,对女人说:“你记得不那年我弄死的那个狐子”“咋”“那是个白狐子。人说千年白,万年黑。那东西成精了。你想,我弄死它,它能饶我”兰兰一听,紧张起来:“咋”白福叹口气:“神婆说那两个死去的娃儿是人,白福把眼睛对准引弟。引弟睡得正熟,脸蛋很红。“还能是谁”白福说,“我们屋里,还能是谁”说着,他撕着自己头发,长叹一口气。“你是说,引弟”半晌,兰兰试探着问。“不是她,是谁”白福气哼哼说,“你不想,一生下她,两个全死了。再说,你不想想。她正是我弄死狐子后生的。你没听瞎仙喧的征西吗苏宝童一被樊梨花打死,就钻进她的肚子,转的薛刚。后来,叫他弄了个满门抄斩。薛家几百口,一下子,完了。他的仇也报了。”“不会的。”兰兰说,“我的娃这么乖,咋是狐子转生的不会的。”“咋不会”白福忽然气恼起来:“难道我白嚼她不成你不想想,她那个精灵样子,哪像你,哪像我我们两个榆木脑壳。你不想想,那些口歌儿,她一听就会;村里那些娃儿,哪个有她脑子灵光”“就这呀那你说爹脑子好不妈脑子好不咋灵官脑子好使灵官又是啥转生的我不准你胡说”
第十四章2
白福瞪一眼兰兰:“灵官的脑子好个屁套牛犁地,学了三天,都没学出个眉眼。好个啥好的话,咋不考个大学白供他十几年,白吃了几十筐烙锅盔。哪像引弟”引弟醒了,一轱辘爬起来,问:“我咋了,我咋了”“睡你的”白福吼一声。引弟吓得钻进被窝。兰兰搂住引弟,自言自语似说:“我的引弟这么乖”她拍拍引弟的屁股,对白福说:“我不爱听这些话,以后别说了。”灵官妈进来,说:“大年正月的,喝神断鬼啥哩想停了,停一会。不想停了,看打牌去。”白福黑了脸,瞪一眼兰兰,冷哼一声,就捂了头,脑中却老晃着梦中的场面。白福断定媳妇肚里怀的是儿子。征兆十分明显:一来女人爱吃醋,酸男辣女;二是她进门先迈左脚,男左女右;三是他在八月十五那夜拔过人家地里的一个箩卜,没有一个裂口,反倒多出个蚕儿尖尖,极像他朝思暮想的儿子才有的那个牛牛;四是十月初一他到雷台湖去,一个神婆子一见就说他今年准得贵子只是不好活,有人克,吓得他舌头都干成山药皮了,花了五十元钱,才买了个方子:在媳妇的枕头下放个刃口家什,像斧头或刀子,并用祭神用过的红布,做个肚兜,缠到媳妇腰上。可他还是做了坏梦。白福心中胀满了烟。他懊悔地想:“该干的啥都干了。红布也缠了。咋还做这种梦日怪。”他听到女人和引弟叽叽咕咕说话,说几句,还笑,声音尖噪噪直往他耳朵里钻。他一把撩开被窝,恶声恶气说:“笑个屁到门上笑去。”兰兰说:“不爱听,你出去呀。谁又挡你来爹早就出去了。这会儿,要不是天阴,太阳都到半天了。”白福握了拳,很想扑上去揍她一顿,但因在她娘家门上,暂且忍下这口气。再说,自己也确实不想睡了,就穿了衣服,胡乱洗把脸。出得门来,雪光耀目。树上也结了朵朵雪花。风冷嗖嗖吹来,直往骨缝里刺。身子渐渐冰冷了。白福把衣襟裹紧,深一脚,浅一脚,咯吱咯吱,进了北柱家。北柱家早已喧闹起来了。炕上坐满了人,似在挖牛九赌钱。猛子也在那里咋呼:“抓放心抓这么好的牌,不抓,还等啥”猛子旁边是狗宝。一见白福,狗宝的神色很古怪,像微笑,也像嘲弄。白福觉得他在嘲弄,心中有股气腾起,很想揍人,便对猛子也带了气:他竟然和狗宝在一起,哼
第十四章3
因过年,抓计划生育的松了,凤香便回家了,正坐在炕沿上纳鞋底。她一下下把麻绳扯出老长,扯出一缕缕超然物外的嗞嗞声。见白福颠个脸,便用下巴点点脚下的小凳,示意他坐下,问:“听说兰兰伤了胎气。不要紧吧”白福说:“不要紧。”凤香说:“那个疯子,还咬人呢。”抿嘴笑了。白福望望她嘴上的几处伤痕,也笑了。这一笑,腹里积蓄了一早晨的不快消失了。凤香望望屋里人,压低声音说:“过完年,听说又要抓。小心些,最好躲出去。听说高沟抓了九个,抓上就往手术台上按。没治。”白福哼一声。炕上挖牌的人忽然哄笑起来。猛子大声说:“嘿,咋着哩我估摸人家有两副鱼子。你还不信,硬抓,硬抓,老沟滚大了。”北柱说:“驴屁。你明明叫我抓。我本来不想抓。”猛子直了嗓门喊:“这么好的牌,不抓,饶了他了。要不是他有两副鱼子,还钻了尻子了”凤香努努嘴,说:“瞧,就这样子。头都聒麻了。”说着吼一声:“悄些成不成再嚷,到院子里玩去。”猛子说:“你烦了,到院里去。”凤香说:“哟,我的家还由不了我了你还硬三霸四的。”猛子说:“你再说再说叫五子把舌头咬下来。”凤香扬起鞋底,在猛子的背上狠狠扇了几下。猛子夸张地哎哟几声,说:“打是亲,骂是爱。小心北柱吃醋。”凤香笑道:“那我就多亲几下。”又结结实实扇几下。猛子滚到炕角里直哎哟。北柱笑道:“我也希望五子把那块喂猫儿的肉咬下来。一天到晚,叽叽喳喳,脑子都聒麻了。”转头问白福:“你不摸几把想摸就来。我可不中了,再输,就搭上女人了。”狗宝问凤香:“听见没再输就该你上了。你当然方便得很,裤带一松,就当钱。”凤香道:“成哩,成哩,你舔也成。你能说出,老娘就能干出。”人们都笑了。白福说:“你们玩,我没那个心思。”北柱说:“放心玩,今日有酒今日醉,管他明日喝凉水。有啥放不下的不就是没个娃子吗有娃子能咋样能生下,生他一个。生不下,也不管他。吃照样吃,玩照样玩。”狗宝接口道:“就是。活人嘛,该松活的时候,就松活一下。”说着,望了白福一眼。这一望,自然是和解的表示,但白福心里仍不能原谅狗宝,便不理他,对北柱说:“我还有些事呢。”“啥事呀”北柱道:“老天爷叫老子们休息呢。”凤香劝白福:“想玩的话,就上去玩去,反正也是玩艺儿,又不是大赌,没啥。”白福摆摆手说:“不,不,我真有事呢。”顺势出了门。2凉风水一样泼来,洗尽了北柱家留在心头的一点喧闹,白福感到了清爽。地上白茫茫的,很刺眼。天空灰蒙蒙的,还有零星的雪花在飘。白福很喜欢踩到雪上的感觉。只有在这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强有力的。其他时候,总觉得自己很猥琐。
第十四章4
走一阵,他又想到那个梦,浓烟又从心里腾起。真是糟透了。那话题简直成克星了,一出现,脑子便灰了。一条黑狗从巷道里蹿出,吓了白福一跳。后面跟两条狗,一条白狗,一条花狗,像追姑娘的小伙子一样兴奋,旋风似远去了。白福一阵怅然。他想,要是人像狗这样多好啊,无忧无虑的。他,别说撒野了,连快走几步的心情也没有。花球走过来,见了白福,问:“你干啥哩告天爷吗”白福笑笑。花球说:“走,挖牌。”白福说:“北柱家正挖呢。”他想到了自己的梦,就说:“你念的书多,你说梦是咋回事”花球说:“咋回事尻子盖不严就作梦。”白福说:“别开玩笑。”花球道:“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啥,就梦啥。”白福说:“你看过梦书没”花球笑道:“啥梦书”一指齐神婆家:“她会圆梦呢,问啥也知道。我嘛,瞎编可以,算不得数的。”说着,走向北柱家。白福想:就是,咋没想到她齐神婆正偎在炕上嗑瓜子,旁边还坐着来串亲戚的一个老婆子。一见白福,神婆便招呼道:“快来,上炕,上炕,炕热得很。”白福跺跺脚上的雪,说:“干妈,你焐你的。我不冷。”齐神婆抓过一把瓜子。白福接了,却不嗑,攥在手里,听她们喧慌。不一会,就攥出汗水,把瓜子弄湿了。白福听了一阵,才听明白她们在喧一桩保媒的事。本是件无聊小事,她们却喧得很投入,你唱我和,竟将白福冷清清撇一边了。白福只得耐住性子听,听了一阵,却听了进去。他很佩服齐神婆,一件一目了然的简单小事,却能渲染出许多色彩,而且语言很是鲜活。“有啥事说。”齐神婆忽然转过身来:“我知道你无事不找我老鬼。”白福本已专注于她们的喧谈了,她这一问,倒叫他一下子回不过神来。就是,啥事呢他想了一阵,才想起那个梦,就说:“也没啥,做了个梦。”齐神婆笑了:“我当又是啥大事呢谁不做梦呢。”“可这梦很怪”白福说。他喧了梦的内容和那年打死白狐子的事。“千年白,万年黑。”那个老婆子接口道,“你不该打的。人家已修成了仙家。”齐神婆望一眼白福:“瞧,咋的那年,我就说你惹下祸事了。”她又对老婆子道:“他的几个儿子都没养活。”“不该打。人家是仙家,敬还敬不及呢。”老婆子重复一句。“都这么说。可打的已经打了,咋办骨头都化成灰了,叫我咋办”白福灰了脸,说:“要煮要烤,也只好由它了。”两个老婆子互相望望,没说话。白福颠着脸,拧眉一阵,吭哧半天,说出了自己的怀疑:“我估摸引弟那丫头,是狐子转生的。”
第十四章5
齐神婆咧嘴笑了:“瞧他急的,啥念头都有了。”又对那老妇说:“反正,他那丫头,可精灵得很。才几岁,啥都会干,会剪花,会唱口歌,长得红处红,白处白,眼珠一转,倒真有种狐媚气。”老婆子也笑了:“那敢就是狐子转世了。”“你们别笑,可真是的。我咋想都觉得那丫头不对劲,她一生下来,娃子就没活过。还有,我做梦老梦见她长个狐子尾巴。”老婆子说:“别胡思乱想了。就算真是狐子转生的,又有啥该咋还是咋。不过,你那个梦倒真不太好,还是得生个法儿。”“就是。”齐神婆接口道,“该生的法儿还得生。”白福哭丧着脸道:“啥法儿还有啥法儿该生的方儿都生了。干妈也整治过几回,可不顶事。啥事儿也没顶。”“那你还来干啥”齐神婆沉了脸,“老娘是没本事,又没有寻到你门上去找你。以后少上老娘的门。”白福变了脸色,跺跺脚道:“嘿,我说的是其实还是有效果,前一个生下就是死的,干妈燎过后,后一个活了一月呢。”老婆子道:“着,这不就是效果吗”白福道:“可”齐神婆颠个脸,眯了眼,说:“实话告诉你,老娘的桃花镇法用了百次,灵九十九次,只你家一次不灵。为啥有人克。你心里也该清楚,我的话也只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也别再来找我,找也没用。”白福傻了,双手抱拳,连连作揖,“干妈”叫了一大堆,眼泪也下来了。“真不成。”齐神婆冷冷道:“亲里亲戚的,我也不能哄你。我的道行没人家的大,就这。人家是要债的,我也只是尽尽人力,没治。我真是没治的,回去吧。”“干妈,你不是要我的命吗”白福抹一把眼泪,嗓子里咯噔一阵。“你不管,不是要我的命吗”又跪在地上,乓乓乓磕几个响头。神婆却闭了眼睛,理也不理。老婆子说:“起来,一个大男人,像啥样子我听说,千年的狐子啥都不怕,就怕一个白骟狗。都这么说,你弄上一个试试。”“又到哪里弄白骟狗呀”白福哭丧着脸道。3“呸”白福的话音没落,孟八爷就哈哈大笑:“屁股没盖严做个梦,也用得着这样掏心挖肺瞎折腾啥千年白,万年黑呀那是人瞎说的。我见过一窝黑狐子,刚生下的黑狐子。你说,它真活了一万年屁胡子。那是黑狐子种。活个几十年,至多。我不信能活上万年。倒是有些通灵的狐子活得长。人家也练功呢。初一十五拜月亮,练出狐丹,寿命就长了,也会变个啥俊姑娘。听说这种狐子,一怕雷殛,到一定时候,天雷要殛它。躲过这一难,就成气候了。
第十四章6
“当然,它怕白骟狗,就像多大的老鼠也怕猫,天生的。白骟狗煞气大,多厉害的狐子,一见它,也厉害不起来。老一辈,都这么说。当然,谁也没有见过啥千年狐子。这年头,狐子能过上个几年就不错了。人的眼睛一个比一个亮,见个踪踪子就追。它想活,也活不长。你想,它们连自己的命都做不了主,还能报复谁呀“听老年人说,凉州城有个老满州,衙里当官。他就有个白骟狗。一天,一个猎手来找他,要借白骟狗,说是自己瞅下了一只千年白狐子,咋也打不下。明明见它在一个地方,一举枪,就不见影儿了。听一个道人说,千年的狐子最怕白骟狗。就来向老满州借。老满州满口答应。“夜里,一个白胡子老头来找老满州,叫他不要给人借白骟狗。老满州说:成,不借就不借。明日,我带上它上衙。老人就吃碗黄米面条,走了。第二天,老满州把狗拴到后院,吩咐家人:猎户来,就说我带上衙门了。唉,也该着那狐子遭难。猎户一来,便听到后花园里有狗叫声,就隔墙弄出狗来。一到坟滩,白骟狗直溜溜扑过去,把白狐子按住了。扒开狐肚子,黄米面条儿还没消化呢。原来,那个白胡子老汉是狐子变的。“后来,白狐子报复了,老满州全家遭了殃,人死了,家败了。谁叫他说话不算数呢。哎,咋给你讲这些白福,白福你怎么了,脸煞白煞白的。别往心里去。说是这么说的,谁又见来屁胡子。说这些干啥哎白福,你怎么了白福白福”4引弟很高兴。因为,从来对她恶声恶气的白福忽然待她好了。引弟脆生生地笑,奶声奶气地唱那些“口歌儿”:“点点斑斑,草花芦芽,打发君子,出门一个。”引弟不知道“君子”是啥东西,但仍是很起劲地唱。她好高兴,差点儿把自己攒钱给妈妈肚里的小弟弟买布娃娃的事告诉爹。爹真好。爹好起来比妈还好。妈只是搂了她,一晃一摇地教她唱“口歌儿”。爹却肩上扛了她,到蔺家铺子里买好吃的。爹问:“引弟,你想吃啥”引弟不敢说话。爹又问了几遍。引弟才大着胆子说:“方便面。”爹说:“哟,你的口味还不低。再呢再想吃啥”引弟就小眼瞪大眼了。因为,她实在想不出还有啥比方便面更好吃。爹就说:“成。就吃方便面吧。美死个你。”就摸出两块钱,买了三包。引弟吃了一包。可香呢,香到脑子里了。她还想吃一包,可再也舍不得“独吞”妈老这样骂爹了。为啥留给妈妈肚子里的小弟弟呀。还有一包,引弟省给了妈。妈没吃,却望爹,说:“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爹说:“你望啥给娃吃点,心疼”妈说:“着。你也算当了回老子。”又望了爹好一阵,却叫引弟把那包方便面给了爷爷。爷爷接了,泡了,轰轰隆隆吃了个精光。引弟不明白,妈为啥不吃方便面多好吃呀妈真是个苕包。不过给爷爷也好,爷爷多瘦呀爷爷老想做大买卖,费脑子,才那么瘦。爷爷可馋啦,老想吃肉,老嚷嚷,一嚷,奶奶就颠了脸骂:“想吃了,下辈子转生个狸猫儿。”引弟又听得妈问:“赢了”
第十四章7
爹哼了一声,说:“给娃买点吃的,问啥”“怪。当了几年老子,还没疼过娃呢。这回,你总算长了个人心。”妈说。爹还扛了她,去乡上的大商店,买了套花衣裳。蓝花花,白点点,好看得很。引弟想留给妈肚子里的小弟弟,可爹硬叫她穿。引弟只好穿了,心里念叨:弟弟,可怪不得我呀。以后,你还有更好的呢。爹肯定会给你买的。引弟还从来没穿过这么好看的衣服呢。村里娃儿都围了来,用脏手摸,引弟就东躲**的,可还是粘了不少土。引弟想:爹要骂呀。可还好,爹望也没望她。只是,引弟不明白,爹为啥老阴个脸引弟希望爹笑,可爹总不笑,引弟就只好悄声没气了。爹见了,却又逗她笑。怪的是,她一笑,爹就不笑了,就叹气。引弟忘不了爹说过的她“刻”弟弟的话,但总是不明白她咋个“刻”法,是不是像拿了小刀刻木头那样“刻”呢她可没拿过刀呀剪呀的。一拿,妈就一把夺过,怕伤了她。那为啥说她“刻”呢想问爹,又不敢,就问妈,问莹儿姑姑,问奶奶,得到的回答总是:“小娃娃家,胡问啥哩”引弟虽不知道咋“刻”可知道“刻”肯定是叫爹爹不高兴的东西。爹的天门脸上老是有几道深深的肉槽儿。引弟想,莫非,那也是“刻”的引弟多想叫爹笑呀。可爹总不笑,买了衣服给她时,也只是脸上的肉动了一下,引弟明白,那便是爹的笑了。引弟想,咋能叫爹高兴呢唱个“口歌儿”试试,因为她自己一听“口歌儿”就高兴得想跳,想笑,想来爹也是。于是,引弟就唱了麻地里麻,沙地里沙。王哥拾了个花手帕,给我吧,不给了罢你骑骡子我骑马。一骑骑到舅舅家,舅舅门上两朵花引弟最爱唱这个“口歌儿”,这是莹儿姑姑教的。村里娃儿都爱听,她一唱,身前身后,就能围一大堆娃儿。可引弟发现,爹不爱听。她一唱,爹的脸就黑了,就怪怪地望她,虽没骂,引弟还是能看出,爹不喜欢听。怪,这么好的口歌儿,爹咋不爱听是不是嫌我唱得不好也许。因为这几天,她嗓子哑,声音沙沙的。说话时,没以前脆活了。引弟就想,嗓子呀,快些好吧,好给爹脆脆地唱“口歌儿”,唱得他也笑。引弟想:咋能叫爹高兴呢一天,奶奶问她:“引弟,这回,你妈生个啥呢”
第十四章8
引弟就比了个男娃儿尿尿的样儿,说:“这回,生这个这个”奶奶笑了,对爹说:“娃娃的嘴里有实话呢。”引弟看到爹笑了。引弟才知道爹喜欢听这话。为叫爹高兴,她就老做那样子,老说那话。爹却又黑了脸说:“行了行了,烦死了。”引弟就不说了。她不明白,同样的话,同样的动作,为啥爹又不高兴了引弟多想叫爹高兴呀,可没治。她不知爹的心是咋长的为啥总阴个脸,会憋出病来的呀。为叫爹高兴,她就把布娃娃的事告诉了爹,可爹只是脸上的肉动了动。这回,引弟看得出,那不是笑。咋办呢引弟想疼了脑袋,才记起爹只是在玩麻将时才高兴,当然是赢的时候。可妈不喜欢爹玩。爹一去玩,妈就颠个脸,爹一回来,妈就数落。一数落,爹的脸就黑了。有时,黑了脸的爹就打妈;有时,爹啥话也不说,捞过被子蒙了头,死睡。引弟怕爹的黑脸,也怕爹的死睡。爹一死睡,引弟就悄声没气了,不敢唱“口歌儿”了,连走路也垫了脚尖,怕惊动了爹。因为这时的爹,是吃了**的,见个火星儿就会爆炸。一爆炸,连亲娘老子也不认。引弟就想,妈不好,妈不该数落爹。爹不就是爱玩个麻将吗那有啥只要爹高兴,叫他玩去,谁不爱玩呢连引弟都爱玩,爱玩“藏猫猫”,爱玩“跳沙包”,爱玩“老鹰捉小鸡”,爱玩“姑妈妈过家家”,但引弟最爱玩的是:和妈妈面对面坐了,捞了妈的手,你捞过来,我推过去,一俯一仰地唱打锣锣,围面面,舅舅来了擀饭饭,擀的什么饭饭擀的红豆豆饭饭。擀白面,舍不得;擀黑面,舅舅笑话哩;杀母鸡,下蛋哩;杀公鸡,叫鸣哩;杀鸭子,鸭子飞到草垛上,孵下了一窝老和尚;背一个,扛一个,过沟去了踒死个,家里还有十来个引弟最爱玩这,一玩,妈就笑成个小姑娘了。引弟想,爹当然也有他爱玩的了。只要他高兴,玩去。不叫玩,爹会闷出病的。引弟知道妈不叫爹玩的原因是爹老输钱。输钱当然不好,一输,爹的脸还是黑了。可总有赢的时候,一赢,爹就比妈好。爹就会搂了她,举过头顶“引弟,引弟”地叫,时而,吧唧一声,亲得引弟的脸痒酥酥的。
第十四章9
引弟打定主意:以后,把灵官舅舅、莹儿姑姑、还有爷爷奶奶过年时给她的福钱偷偷藏下一些,再也不全部给妈妈交了。把那些分钱儿啦,角票儿啦,全偷偷留下,存在那个黑罐罐里,悄悄藏在柜底下。爹啥时闷了,没钱打麻将了,就取出一把,悄悄塞给爹,给,爹想玩的话,玩去。引弟偷偷笑了。她想,爹一定很高兴,一定会像赢了钱一样,把她举得高高的,一定会说:“哟我的引弟,懂事了。”边说,边在她的脸蛋上吧唧。引弟笑出了眼泪。引弟于是劝妈。她说,妈妈,爹爱玩,叫人家玩去。人家心里闷呢,可别闷出病来呀。妈就搂了引弟叫乖乖,说:“丫头,你还小,不懂,那可不是一般的玩,那是个无底洞呀,能把我的乖乖填进去,能把爷爷奶奶填进去,把妈填进去,把房子啥的都填进去,还填不满呢。”引弟当然不信。她说妈妈骗人,爹玩的时候,哪见个啥洞又问,妈妈,你说的洞是不是方块块上的那个圆点点妈说不是,你还小,长大后,你就知道了。引弟虽不信妈说的吓人的话,但还是知道爹玩时要花钱。也许,她将来的钱罐罐里存下的不够爹花,就想,等我长大了,挣好多好多的钱,叫爹玩个畅快。引弟听灵官舅舅们喧过,说一个叫双福的舅舅有好多钱,有树叶子那么多。乖乖她就问妈,双福舅舅那么多的钱也填不满吗妈就笑了,说死丫头,你在哪个磨道里听了个驴的梆声人家双福,当然能填满。引弟就说,那我长大,就挣双福舅舅那么多的钱,叫爹玩去,没明没黑地去玩,想玩啥,就玩啥。可,我只叫爹输。妈问为啥引弟说,他一赢,别人的爹爹又高兴了。妈就一把搂了引弟,哟,我的引弟,人不大,心还不小呢。自那后,引弟就发愁了:她啥时才能长大呢啥时才能像双福舅舅那样挣钱叫爹高兴地玩呢5这天,日头爷才偏西,白福就悄悄对引弟说,走,引弟,爹领你玩去。于是,引弟就像麻雀儿一样跳了,边跳,边拍小手。她想,可能是妈把她长大后挣钱的事告诉给爹了,爹一高兴,才领她去玩。她想问妈,可妈妈给爹打发到乡上的大商店里买东西去了。引弟很羞。她想,妈真是个“漏嘴子”,盛不住个话。臭妈妈,以后,再也不给你说心里话了,臭妈妈。但引弟还是很高兴跟爹去玩。天很冷。阴洼里还有雪,白白的。引弟很喜欢雪,很喜欢脚踩在雪上咯吱咯吱的声音,还喜欢和妈妈堆个雪人,再插个葫萝卜当鼻子。那个鼻子好长呀,逗得妈妈咯咯地笑。妈就揪住引弟的鼻子,说:“长长”妈也想把引弟的鼻子也拉那么长。一开始,引弟吓坏了,老照镜子,总怕长个怪怪的长鼻子。一夜,鼻子真长了,哎呀,老长老长,怕有大白杨树那么长了,一头儿还活了似的,一蹿一蹿不停地长。她吓坏了,就吱吱哇哇地叫。妈妈叫醒了她。哎呀,原来是个梦。第二天,给奶奶一喧,奶奶就说,别听那个妖精的话。奶奶老在背地里骂妈“妖精”,可引弟也没给妈说过。引弟想,我才不当“漏嘴子”呢。
第十四章10
引弟想,爹想和我玩啥呢当然,最好是打雪仗了。一下雪,引弟就和村里娃儿打雪仗。团个雪球,扔过去,“啪”就开花了。那时,引弟的小手就冻红了,小脸也红了。一出气,嘴里就冒烟,一股子烟,又一股子烟,可像爷爷抽烟了。有时,引弟就举个木棍儿,学爷爷抽烟,她猫了腰,咳嗽几声,“啪”吹出一股子白气,再“啪”吹出一股子白气,逗得爷爷哈哈笑。阴洼里的雪很薄,堆不成雪人,看来也打不成雪仗。但引弟还是很高兴,不管咋说,总是和爹在一起。可爹,为啥总是木着脸呢。走一阵,叹口气,走一阵,又叹。引弟想,爹为啥不像妈妈那样笑呢妈妈笑起来像引弟,有时还抱了肚子,满炕滚呢。可爹就没这样笑过。妈好开玩笑,爹就恼。一恼,妈就唱:“春风不解风情,吹疼了少年心。”妈老唱,老唱。后来,连引弟都会唱了。“引弟,爹好不”白福忽然发问。引弟仰了小脸,望爹。爹奇怪地望她。爹从来没这样望过她。她想,爹咋这样问呢还用得着问吗爹当然好,哪有不好的爹呀爹打也罢,骂也罢,总是爹。奶奶不是老说,打折骨头还连个筋丝儿呢,就说:“当然好呀。”“恨爹不”爹又问。爹仍然那样奇怪地望她,眼窝里湿湿的,像是哭了。引弟晃晃脑袋,想:爹为啥这样问呢是不是妈又当漏嘴子了上回,爹打妈,引弟就对妈说她恨爹。臭妈妈,你为啥老当漏嘴子呢就说:“恨过的。那次,你用牛鞭打妈妈。妈妈身上,尽是血口子,一道一道的。吓死我了。爹,以后,不要打妈了。妈老偷偷哭呢。你气了,打我,用巴掌扇尻蛋子,美美地打。尻蛋子上软肉多,打不坏。别处,不行。一打坏,可没人给你挣钱了。”引弟差点要说出像双福舅舅那样挣大钱的话了,好容易才忍住了。“好,丫头。爹答应你,以后,不打你妈了。可有时,爹也忍不住,爹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了,就这么个炒麦子脾气,忍不住。可爹的心好。丫头,你信不爹的心好。”“爹当然心好。不好,咋能当爹爹”引弟奶腥呵呵地说,“妈妈说,把我养这么大,可不容易哩。妈妈说,刚生下,像个精肚老鼠儿呢。怪,我咋像精肚老鼠儿呢我不相信那个臭妈妈的话,谁叫她是个漏嘴子呢。”白福却忽地捂了脸,蹲在一个沙丘上不知不觉间,他们已靠近沙窝了。白福的肩头抽动着,好久。引弟吓坏了:“爹,你怎么了怎么了爹爹”白福却忽地站起来了,眼窝湿了。他使劲擦,却越擦越多,脸上水哗哗了。
第十四章11
“爹你怎么了”引弟带哭声了。“打了个虫子,眼睛里。”白福说。“哎呀,那可难受了。上回,我也打了一个。哎呀,那个涩呀,那个酸呀,眼泪一股子一股子淌。妈用舌头舔呀,舔呀,才好了。爹,舌头一舔,绵绵的,真舒服。来,爹,我给你舔。”引弟呸呸地吐了几口唾沫,“妈妈说,把嘴里不干净的吐净了,才能舔。来,爹,一舔,就不难受了。”“不,不了。”白福说。他的身子摇摇晃晃,好容易才站住了。“引弟,想不想玩了不想玩的话,就跟爹回家。”“玩呀。爹,咋不见蚱蚱爷呀”“那东西,夏里才有。”“多会儿等到夏里呢顺爷爷说,老鼠吃蚱蚱爷,狐子吃老鼠,人又打狐子。爹,人为啥要打狐子呀,狐子多好。”“好个啥呀那玩艺儿,害人精。想玩的话,那就来吧,爹背你。”白福的脸又黑了。白福见引弟的小脸蛋红了,就脱下棉衣,裹住引弟身子,背起她,大步流星地走进沙窝。6引弟好高兴。爹背了她,她立马就天一样高了。引弟就见到了一个很亮很白的日头爷,像冰做的盘子。还有几朵云,丝丝缕缕的,很像妈破了的那块白纱巾。引弟很爱那白纱巾,举了它,一跑,风就“呼呼”地把它吹身后去了,很好玩。可后来,爷爷把白纱巾绾了驴笼头了。引弟伤心了好几天。一看到那几片云,引弟就想起了纱巾,心里又噎巴巴了。她就发现自己又做错了一件事:不该要方便面。方便面虽香到脑子里了,总是一阵阵。肚子一饿,方便面肯定也就没了。浪费钱。她应该叫爹给她买个纱巾,红的也行,白的也行。妈喜欢白的,引弟喜欢红的。但妈既然喜欢白的,那就买白的吧。买个白纱巾,也就像买了两个东西:妈想围了,围去;引弟想玩了,就举了它跑,叫风“呼,呼”地吹。引弟很后悔,她很想问爹,啥时再给她买好东西吃呢那她就不要方便面了,馋死也不要,香到脑子里也不要,拚命忍住,就要纱巾。妈妈早没纱巾围了,买了,妈肯定高兴,眼睛又笑成个鸽粪圈儿了。但引弟还是没敢问,她又想起了奶奶常说的一句话: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想,我可真不懂事呀。爹连个袜子都舍不得穿。可你,才吃了方便面,又想纱巾了,贪心鬼。四下里尽是沙山。沙山多,沙山大,沙山高,高到天上去了。日头爷都给比下去好大一截子,比刚进沙窝时矮了许多。趁爹上一个沙山的当儿,引弟回头望望后面的路,呀,能看见村子了,隐隐幻幻的,房子像火柴盒那么大。
第十四章12
引弟还看到了几个高烟洞,黑烟正一股子又一股子地往上冒呢。引弟想:那房子肯定也像爷爷,是个大烟鬼,一冒烟,就啥也不顾了。只是爷爷会吐烟圈。爷爷的烟圈吐得可好啦,有大的,有小的。吐大烟圈的时候,爷爷嘴一鼓,眼睛一瞪,嘴张得大大的,不出气,舌头“哗”地一送。哎呀,一个大大的烟圈就飞上天了。吐小烟圈时更好玩,爷爷美美吸一口烟,嘴角里开个小洞,再用指头“嘚嘚”地敲腮帮子,一串串小烟圈就飞出来了,好玩得很。只是爷爷近来老忙“大买卖”,不忙时,也老阴个脸,引弟不敢缠他了。那烟洞笨,肯定不会吐烟圈。瞧,那烟,直溜溜上天去了,也很好玩。引弟就想起了莹儿姑姑的一个“口歌儿”:“烟洞里的烟,直冒天。黄河里的水,洗红毡。红毡铺,七姑娘舞。”忽觉得爹的身子摇晃了。引弟想,爹扛不动了,就说:“爹,放我下来,我自己走。”爹咳嗽几声,说:“你稳稳地坐好吧,丫头,你长这么大,爹还没背过你呢。爹背你,好不好玩”“当然好呀。”引弟觉得爹好高,高到天上去了。爹的肩膀那么宽,爹的力气那么大,比天还大呢。力气大好,人都说爹干起活来像个犏牛。胡说。犏牛哪有爹的力气大。犏牛能像爹那样拉个架子车,装得山一样高,轰轰隆隆地上那个大坡肯定不行。哼,那些犏牛,慢慢腾腾的,死眉死眼的,能和爹比引弟又想,力气大有时也不好,打妈妈时,爹能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妈妈提过来,扔过去,一巴掌,一锤头,妈就支撑不住了。那时,引弟多希望爹没力气呀。她就不停地念叨:天爷爷,叫爹没力气吧,像小鸡娃那样没力气吧可那天爷爷,总不听引弟的话。在爹厚实的肩膀上,引弟晃势晃势地“走”着。她大睁着眼睛,新奇地看起伏的沙山,看蓝蓝的天,看撒在沙山沙洼间的一星星柴棵。好开心。但是一感到开心,引弟就觉得不对了:她的开心,是爹累的哩。“下哩,爹。”她扭动着身子。“咋不好吗”爹的声音闷闷的。“好是好,可爹累。”“不累。丫头,爹没好好地待过你。也怪不着你,谁叫你,不说了,丫头,记住爹的话,别怨爹。”引弟不明白爹的话。爹咋说这种没头没脑的话呢不就是打过我几巴掌吗早不疼了,就说:“爹,你还给我买过方便面呢。你忘了你真好就是,以后,你不要打妈妈。成不”“以后好。爹听你的话,不打了。”7日头爷悬在了最高的那座沙山上。几股子很红的光射来,连引弟的身子也染红了。白福放下引弟,他的头上满是汗,眼窝里也是汗。引弟想,眼窝里咋也淌汗呢她想起妈妈常说的“眼窝里淌汗,手心里起皮”的话,就想,背了我,爹可累坏了。
第十四章13
这是啥地方引弟揉揉坐麻的屁股蛋子,歪了脑袋,四下里瞅。沙山,沙洼,沙米棵,黄毛柴还有许多引弟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引弟终于记起来了:她跟顺爷爷来过这种地方放过羊,叫啥来着对了,叫沙窝。可为啥灵官舅舅叫另一个名字呢不知道。大人的事,小孩子少问,管他们叫啥叫啥去。毕竟打春不久,天还冷得很。引弟的小脸蛋冻红了,小脚脚冻麻了,小手手被爹捏得死疼,但引弟还是很高兴。沙窝窝里好玩,不像村里,尽是坦土,多好的衣服也弄得土眉土眼的。这儿,打个滚啥的,也不会弄脏衣服。看看爹买的新衣裳,已有些脏兮兮了,那是村里娃儿摸脏的。沙窝里好,你想叫脏,都脏不了。引弟喜欢这“沙窝”。白福蹲在沙洼里,木头一样,好久,才问:“引弟,天快黑了,你害怕不你自己说,你玩哩,还是跟爹回去”“玩哩,爹。你瞧,月亮牙牙。顺爷爷说,狐子就拜月亮牙牙呢,就是给月亮牙牙磕头呢,乓,乓,一个一个地磕头。顺爷爷说,磕几百年,就变成姑娘了,可俊呢。不知道有没有莹儿姑姑俊”白福于是望引弟。引弟觉得爹的眼睛很怪,怪得她都不敢望了。她想,是不是我又说错话了这回,我可没说“刻”弟弟呀爹为啥不高兴。但白福马上转过头去了,自言自语地说:“这丫头,看来,就这么个命了也怪不得我。”白福很快地起了身,下了沙洼。不一会儿,就拾来了一堆怪怪的东西,长长的,像黄瓜,好像哪里见过。引弟问:“爹,这是啥呀”话一出口,却想起来了,和顺爷爷放羊时,她见过这东西,顺爷爷叫它“沙驴球棒子”。顺爷爷拿了一个,乓乓地敲。棒子就折了,里面也是沙。“金子。”白福说。“金子是啥”“金子是啥呢”白福皱了眉头,老半天,才说,“金子就是金子,比钱还值钱。指头大一疙瘩儿,买牛大一疙瘩钱呢。”“比双福舅舅的还多”“当然。”白福奇怪地望引弟,“你也知道双福”引弟吐吐舌头,笑了。该不该把这话告诉爹呢长大,她要挣比双福舅舅更多的钱,叫爹玩去,赌去,只叫你输。可爹,一输就不高兴了。爹不输,别人的爹就又不高兴了。这可是个难事儿呀。咋办呢“死丫头。”白福不问了。引弟高兴了。以前,爹赢了钱,就这样骂她,然后才在她脸上吧唧。这次,爹没亲她,只望那堆金子。引弟想,这,能换来多少钱呀莫非,也不用等她长大了但引弟又疑惑了,既然有这么多金子,爹为啥老叫穷呢就说:“顺爷爷说,这叫沙驴球棒子。”白福吃了一惊,前后左右望了几眼,又怪怪地望引弟。
第十四章14
“这个他们那个当然是沙驴球棒子这可是金子呀。”白福拣起一个,狠狠折断,寻了许久,寻出个针尖大小的亮星,说:“瞧,这就是。带回去,用水泡了,把泥清掉,澄下的,就是这。一撮,一撮,又一撮,就一大把了,用铁勺子盛了,放火上烤,一会儿就一大块金子了。”引弟信了。她见过一个铸铝锅的,就像爹说的那样,用铁锅盛了铝,放火上,烧呀烧,一会儿就烧成亮亮的一锅“水”了,往模子里一倒,不一会,嘿,就成个铝锅了。引弟想,以后,妈妈就不愁钱了。爷爷奶奶也不愁钱了,莹儿姑姑好多人就不愁了。自己也不用长大了。天天来背这有金子的沙驴球棒子,背回去泡了,澄了,换了钱引弟想痴了。忽然,她说:“爹,你坏”白福吃了一惊,脸白了,又望望四周。“你为啥不早说呢,这么多金子。爷爷就愁不白头发了。”白福不知说什么好,张了口,很蠢地望引弟。“这这”引弟拧了眉头,想一阵,才笑了:“我知道,人参娃娃”“啥人参娃娃”“这东西,也像人参娃娃。莹儿姑姑喧过的。人抓不住,一抓,嗖,就不见了。只有好心的娃娃才能见到。对不对爹。”白福痴了,许久,才叹息道:“精灵鬼。丫头,你是个精灵鬼你咋知道这么多,嘿,还真是的。”“那我就是那个好心娃娃了。我抓了他们,他们会不会死爹,你当那个坏人呀”“哪能呢他们多孤单呀,瞧,这儿又冷那个带回去,洗了身上的脏东西,他们才俊呢。”说着,白福懊恼地晃晃脑袋。他望望悬山的太阳好大会子,嘴里咕咕哝哝,不知说了些什么。“带红头绳没”引弟问。“干啥”“拴呀。那人参娃娃不拴,嗖就不见了,红头绳一拴,他就跑不了。莹儿姑姑说的。这金子娃娃,肯定也这样。”“也好,丫头,我去取红头绳,你就看着他们,别叫跑了。成不”说着,白福忽然哭了,牛吼一样。“丫头,我不是人可下辈子,投个好人家吧。”引弟吓坏了,小心地望一眼爹,说:“爹,我又没说不看的话。爹,你放心去,我哪儿也不去。”
精致生存与eliving一起畅享!
EforEasye从容淡定
EforExcellencee卓越正见
EforElegancee优雅自如
EforEnvisione远见卓识
赞赏